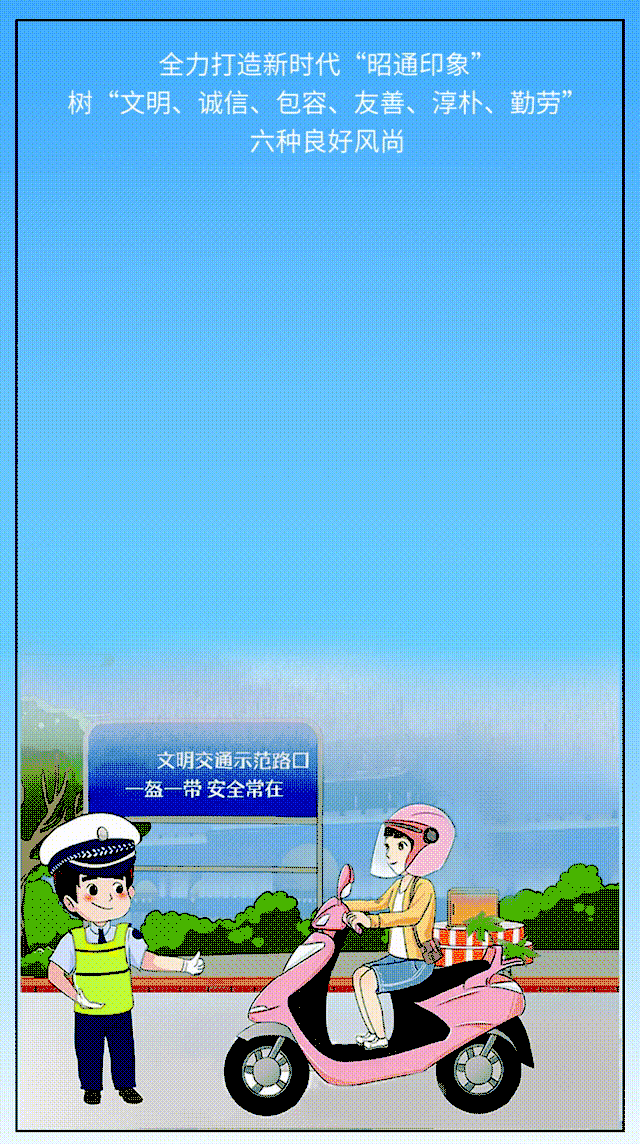2025-11-29 12:27 来源:昭通新闻网



种子的方舟
母亲一个人从昭通老家来昆明。
她临行的前一晚,我忙完工作才想起给她打电话,彼时已经很晚了。电话拨出去后,又担心她已经睡下。意外的是,电话很快接通,我叮嘱她少带些东西,她满口答应。
在环城南路地铁站停车场,母亲下车后,我从网约车司机手里接过行李箱,刚转身要走,却被他叫住:“还有一个。”我愕然地望向车尾右侧,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纸箱。
“这个也是?”我再次向司机师傅确认。
“我带了一箱昭通苹果来。”母亲在一旁说道。纸箱泛着粗粝的褐色,仿佛是从黄土地直接拓印而出的浮雕。
一路上,母亲说这是红富士苹果,因为上市早,可能还有一点儿酸,不是很甜……
我开着车,一边听着母亲的絮叨,一边留意着路况,在车流间隙平稳前行。
母亲用普通话解释“红富士”特性的尾音散落在“春城”的晚风里。
我明明说过什么都不用带,此刻却只能应和一声,默默领下母亲的好意。
每一个苹果都是种子的远征,怀揣着母亲的体温。
流动的水
苹果完成了从枝头到掌心的迁徙,也在旅途中完成了风味的沉淀。而那果核处的晶莹糖心,正是它吸收了故乡暖阳与流水滋养后,凝聚成的记忆与情感。
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一生画过很多树,桦树、梨树、苹果树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画的两幅《苹果树》:一幅是1912年创作的《苹果树1》,枝条向四周延展生长,大有铺展蔓延之势,枝繁叶茂间,绿草、鲜花与丰收的果实笑靥如花,满是盛放的喜悦;另一幅是画于1916年的《苹果树2》,以淡土色为底色,一派秋后肃杀的景象,枝叶紧紧收拢,清晰可见的裂缝如利刃般切割着枯萎衰老的树干,就连果实也是瘦小的、零星的,点缀在萧条、零落、深绿色的枝头上。
树老果瘦,将两幅画并置,恰似人短暂的一生。
此时,我正和母亲待在一起。
母亲刚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纸箱,取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认真清洗干净后递给儿子:“来,吃一个糖心苹果。”
儿子正在看电视,侧脸瞥了一眼,挠了挠头说自己不爱吃水果。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尝尝这份“糖心”,可儿子早已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固执地拒绝了她的盛情。
我看着母亲默默收回被拒绝的苹果,独自大口啃了起来。她没有生气,依旧卖力地“打广告”,叮嘱儿子要一天吃一个苹果。
母亲所说的“糖心”,指的是红富士品种中的糖心苹果。昭通海拔高、温差大,苹果内部的淀粉得以充分转化为糖分,并在果核周围凝结成半透明状的冰糖状结晶,故而得名“糖心”。这种苹果果肉细腻、多汁、甜度十足。
儿子没有接过母亲递来的苹果。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丑苹果”经历过什么,或者说要经历什么才能在果肉深处“窖藏出糖心”,最终来到我们身边。他更不会去思考苹果的缘起与过往,只是简单地说“不要”。疏离感弥漫在房间里,我觉得应当对儿子说点什么。可想说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儿子突然哈哈大笑,他完全沉浸在动画片《小小世界》的喜悦中。
电视的荧光在苹果表面映出冷色光谱。“苹果生青,熟则半红半白,或全红”,我不由得想起《群芳谱》里关于苹果的描摹。然而此刻,它竟然成了情感的隐喻:一半是母亲的热忱,一半是孩子的淡漠,恰似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原本,我可以做很多努力,比如从苹果的形态、色泽、滋味等方面,激发儿子对苹果的兴趣,从而让他欣然接受那份藏在果肉里的“糖心”。
可不知为何,百般纠结后,所有念头都悉数作罢。
儿子还那么小,我却总想让他小而温柔,小而敦厚,像沉甸甸的“糖心”苹果一样,外表或许朴实无华,内里却藏着饱满又温润的内核,待人善良体贴,处事温暖包容。我并非要强求他违背本心,去做那些不喜欢、不情愿的事,只是希望他能学会体谅:哪怕不愿接受,也愿意花上一点点时间,用简单而真诚的话语说明缘由,让拒绝少几分生硬,多几分委婉。母亲递出苹果时的满心热忱,值得被温柔回应;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善意与牵挂,应该被看见。
记忆里的枯叶蝶
在鲁甸县第一中学后面的苹果园里,我和发小背着书包慌乱地“逃生”。
那是粉白色的苹果花开过后不久,同学们都有些跃跃欲试。隔壁班的同学拿着几个仅拇指大小的青苹果,径直跑到我们教室“炫耀”。“蘸点昭通酱,咬下苹果肉”,酸涩的汁水从嘴角溢出,羡煞了旁人。于是,我们挽起袖子、迈开步子,悄悄潜入了苹果园。
绕着苹果园转悠了两圈,确认守园人不在后,我和发小才找到一条小径,通向最近、最低矮的苹果树。就在我们忙着“挑选”跳起来就能摘到的苹果时,我们还是被狗发现了——确切地说,是狗的鼻子嗅到了踪迹。“汪、汪、汪!”狗叫声从小屋那边传来,起初只是偶尔几声,像是在发出预警;紧接着便是连续的、急促的狂吠,“汪汪……汪汪汪……”还伴随着跑动、追逐的窸窸窣窣声,由远及近。
“完了完了!”发小怯怯地说出了我内心闪过的念头。
我们害怕极了——不单是怕被狗追上,更怕被守园人抓到。要是闹到老师那儿,再被同学们传开,那简直是世界末日!她一把拽住我,转身就逃。我们沿着果园墙脚拼命地跑,只想着跑得越快越好,跑得越远越好。
终于,失魂落魄的我们跑到了篱笆洞口,先把书包甩了出去,再紧缩身子使劲往外钻。雨后的黄泥巴又湿又黏,我们也全然不顾,一心只想快点离开。
“狗呢?”
“没追上来,好像被人唤回去了。”
我塞给发小一个小苹果——那是慌乱中从地上捡起来的。
陌生又善良的守园人,用他一声及时的呼唤,让我们保全了“脸面”,不至于被冠上“小偷”的臭名。而我们也在那个湿漉漉的下午,将“是非”二字刻进了心里。
鲁甸老家苹果园泥泞的“芳香”蓦然漫入客厅,儿时的记忆虽已是飘飞的枯叶,但当年守园人的宽容与此刻孩童的懵懂,却在时空中“并行浮现”,瞬间构成我完整的谅解方程式。
糖分是苹果炽热的心。没有心怎么活?异乡人谁不是揣着一颗糖心离开故土的?苹果,是昭通游子沉甸甸的乡愁。
于我而言,苹果是故乡的来信。吃下昭通苹果,我便与远方的故土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对话,所有思念都有了归处。
“把地址发过来,我给你寄点苹果。”诗人朋友芒原兄发来信息。平日里见他发微信朋友圈,在洒渔河畔翻地,在烈日下修枝,在泥泞里施肥、摘果,我们未曾出一点力,却能在秋天准时分享他的劳动果实,心中满是不忍与感激。
我看着手机屏幕,犹豫不决。
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紧接着发来一句:“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心头一暖,回了个“好”。
身处两地的我们忙于工作、生活,在几乎被琐事吞噬得“体无完肤”的时候,苹果熟了!这仿佛是上天赐予诗友间的喘息之机,一次久违的“交流”的良机。
“还写诗没?”
“写的,只是不多。”
“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每年,收取从昭通老家寄来的苹果,成了我秋天里的“仪式”。把苹果取回家后,我会拍照发给寄送人——既有整箱的照片,也有苹果的特写,再附上几句感谢与寒暄的话。
这是陪伴我度过寒冷冬天的苹果。它暗含了多少牵挂与惦记。
我们不再是无根的人。
多年前我资助过的贫困学生明顺,每年都给我寄昭通苹果。
那时我在鲁甸县火德红中学教书。初一年级新生报名时,我负责两个班级的报名工作。明顺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完名没多久,又转身回来找我退钱,说想出去打工挣钱。
我看他的小升初成绩不错,又了解到他是单亲家庭,父亲独自带着他,身体也不好,内心十分不忍。我告诉他:只要好好读书、成绩优异,学校就会发奖学金、助学金,优秀的学生读书花不了多少钱。小小的他听了我的话,决定留下来继续读书。他的认真与努力,让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都对他关爱有加,而我因为岗位变动,不久后离开了学校。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当他向我表达感谢时,我羞愧难当,当时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谁承想事与愿违,没能为他多做些什么。
参军入伍后,他依然坚持给我写信。我从信中得知,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不仅弟弟妹妹们顺利完成了学业,老家还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他问我缺什么,我回复说什么都不缺,心意领了。再后来,他就开始从昭通老家给我寄苹果,说是自家种的,让我尝尝鲜。或许在他眼中,苹果是他最拿得出手的、带着乡音的珍贵礼品。而对我而言,这的确是最合心意的礼物。
我从最初的惴惴不安,慢慢变得“顺其自然”。对我来说,这是他特别的感恩;但于他而言,或许只是从书本中习得的并在成长中养成的良好品行。之前我抗拒收礼物,是固执地认为,资助他本就不图回报。时隔多年突然收下这份感恩的礼物,心里过不了那个坎,既不忍心让他破费,又为当年没能多帮他一点而惭愧不已。
2020年左右,明顺的班主任突然去世,我回老家吊唁时,遇到了当年28班的同学们。尽管很多人已经多年没联系,但他们还是很快认出了我,亲切地叫我“王老师”。
“王老师,这是今年的新品种‘红元帅’,您尝尝。”
我默默品尝着昭通苹果带来的甜蜜。
糖心之问
福楼拜每个工作日都以闻一抽屉烂苹果开始,而我的写作则一直浸润在满屋浓郁的苹果香中。每一天都是爱的劳作,打开书本时,恍若品尝到另一份“糖心”。
高原风沙侵袭、阳光暴晒之下,自然生长的昭通苹果,因表皮多带有果锈瘢痕,常被称为“丑苹果”。它的外表并不出众,放在百果堆里一定不是最显眼的那个,甚至会被一眼掠过,但这并不影响它在风吹日晒中酝酿糖心。无论置身何处,它始终坚守本心,于裂痕中照见光明。
卡夫卡的苹果在书页间腐烂,特洛伊的金苹果至今仍在引发纷争,而昭通的“丑苹果”则在进行着一场甜蜜的抵抗。当学生的“红元帅”翻越乌蒙山脉抵达我的书桌,当希腊雕塑残缺的手掌与我握笔的右手重叠,所有关于苹果的过往与想象,竟在这一刻完成了跨越平行时空的对话。
糖心不是果核的病变,而是大地写给岁月的密码。所有离开故土的苹果,最终都将在某个时刻,化作舌尖上的故乡。
送母亲返回昭通后,我怕她放心不下她带来的苹果的“待遇”。于是去图书馆看书时,我特意带上一个,将它放在书本上拍照发给母亲:“今天带了饼子和苹果出来看书,饿了就吃饼子当早饭,下午再吃一个苹果。”
母亲回复说:“好。”
作者:王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