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08 18:27 来源:昭通新闻网


大崔——
窗外的梧桐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质量审核部办公室的日历也已更换了20余本。大崔坐在靠窗的角落,那是质量审核部阳光最充足的位置,也是他最常待的地方。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泛黄,有着细微刮痕,见证着大崔与文字缠斗的日日夜夜。他的前半生待在这里的时间和在家的时间几乎持平。时光仿佛有着清晰的刻度——从初入报社时被同事笑称“小哥哥”,到如今成为“叔圈”里沉稳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大崔在这个需要极致耐心的岗位上,已然坚守了2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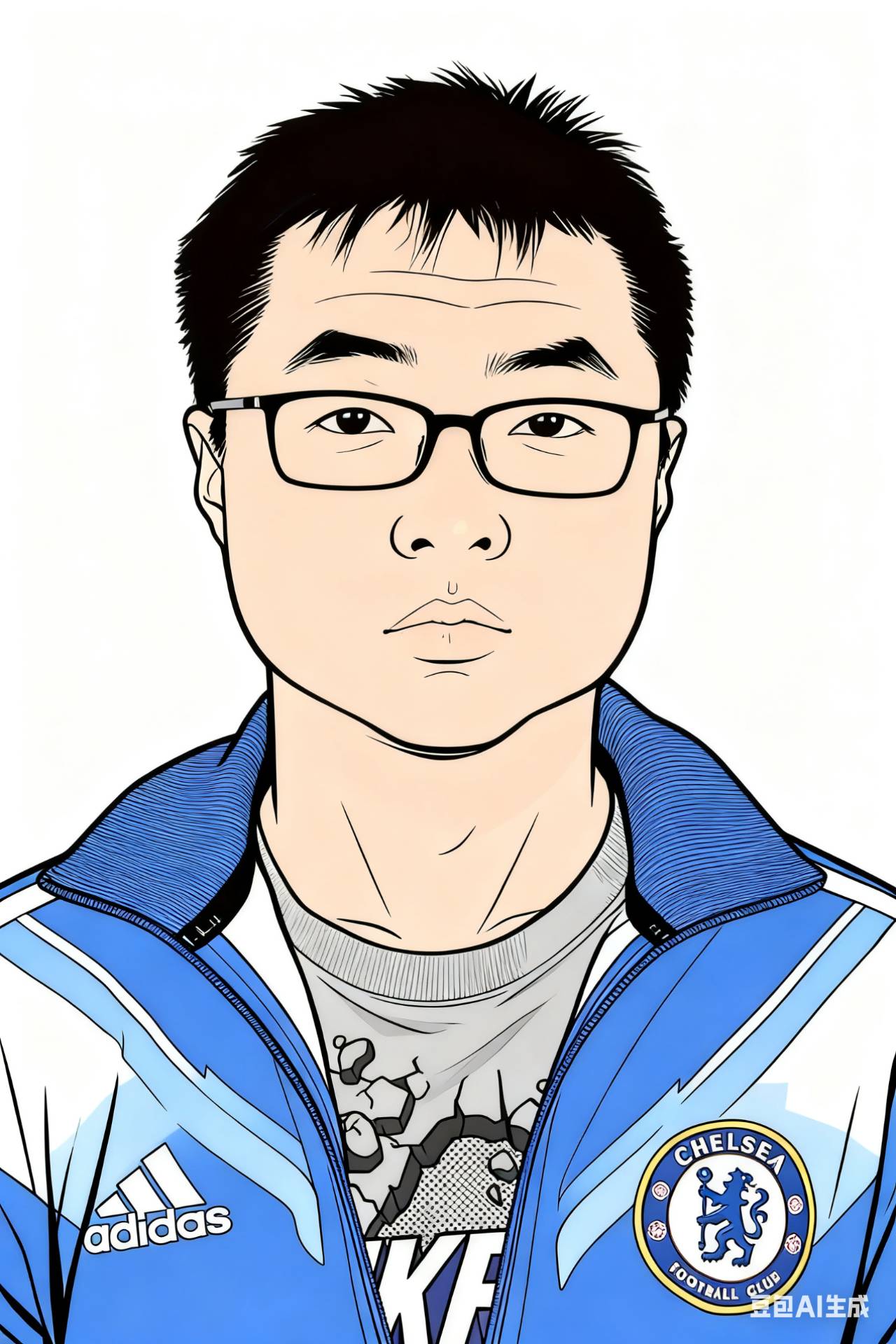
然而,这份需要慢工出细活的坚守,在当下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迫。这份紧迫,首先来自物理时间的挤压。记者、编辑提交稿件必须5分钟之内接稿校对,时间限制像一道无形的鞭影,悬在整个部门的头顶,一天24小时的任何一秒都有来稿件的可能。大崔必须在这种高速阅读中,保持雷达般的敏锐,去捕捉那些潜藏的“敌人”。更深的紧迫感,源于时代节奏对文字本身的冲刷。网络新词、外来语、不合规范的缩写……各种语言现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版面。每当遇到这类词,大崔的动作会有一个微妙的停顿——他需要快速判断,这是需要坚决抵制的“污染”,还是可以适当接纳的“活水”。他时常要放下那本被翻皱的《现代汉语词典》,转而熟练地打开几个权威网站,或是内部更新的词库,进行交叉求证。那本厚重的词典依然是他判断的基石,但已非唯一的武器。
窗外,日光缓缓移动,掠过他那张堆满稿件的桌子。大崔深吸一口气,再次将目光聚焦于眼前的文字。蓝笔在指尖微颤,像一名老猎手最后的警惕。他知道,时间不等人,但有些东西,必须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奋力守住。
沈妹儿——
蓝笔的笔尖,像一只被惊扰的昆虫,倏地停在那个突兀的数字上——“826人?”沈妹儿下意识地皱起眉头,仿佛要凭眉心的力量将那数字拧回原形。她摘下眼镜,世界瞬间模糊成一片疲惫的光晕。用指关节用力揉了揉酸胀的鼻梁,再戴上眼镜,她几乎将脸凑到纸面上,又逐字逐句地审视了一遍原文。没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826”。

一种职业性的警觉让她瞬间进入战斗状态。沈妹儿迅速点亮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查询相关的背景资料和数据记录。屏幕的光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几番比对,疑虑非但未消,反而像墨汁滴入清水,迅速弥漫开来。她不再犹豫,一把抓起了桌上的内线电话。
“妹,今天版面第一段,那个数字有问题。原始数据到底是‘862’还是‘826’?”她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急促。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传来年轻编辑略显困惑,甚至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烦的声音:“啊?这个……我想想吧,等我再翻看一下记录……”那语气里的不确定,像一根细小的针,轻轻扎在沈妹儿紧绷的神经上。她没再多说,默默挂了电话,在突然寂静下来的工位里显得格外沉重。
她抬起手,用力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指尖在皮肤上移动,不经意间,摸到了眼角那几道细密而深刻的纹路。它们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清晰的呢?她忽然有些恍惚。原来,时间真的可以如此具体地磨损一个人。不是用锋利的刀,而是用无数个像这样的情况,被一个可疑的数字、一份亟待核实的来源、一通得不到确切答复的电话所填充的黄昏。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字重量,经年累月,一寸寸压弯了脊梁,刻下了无声的年轮。
她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落回那“826”上。蓝笔,依旧悬停在空中,等待着一个确凿的答案,也对抗着一种正在弥漫的、名为“差不多就行”的习以为常。
小马哥——
小马哥,这个6年前入职时还帅气阳光的大男孩,如今已被岁月与案头工作悄然打磨。他的背影在屏幕前微微向前,像一张拉满了却迟迟不肯放弦的弓。他眨了几下干涩、布满血丝的眼睛,举起那份墨迹未干的校样,胸腔里一口气刚提上来想叹出,却又硬生生顿住——稿纸上,那个刺眼的“反映”再次用错了,这已经是他在这个版面上揪出的第11个错别字。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混杂着职业性的愤怒,在他心口堵了一下。他嘴角牵动了一下,挂上一丝只有自己才懂的无奈苦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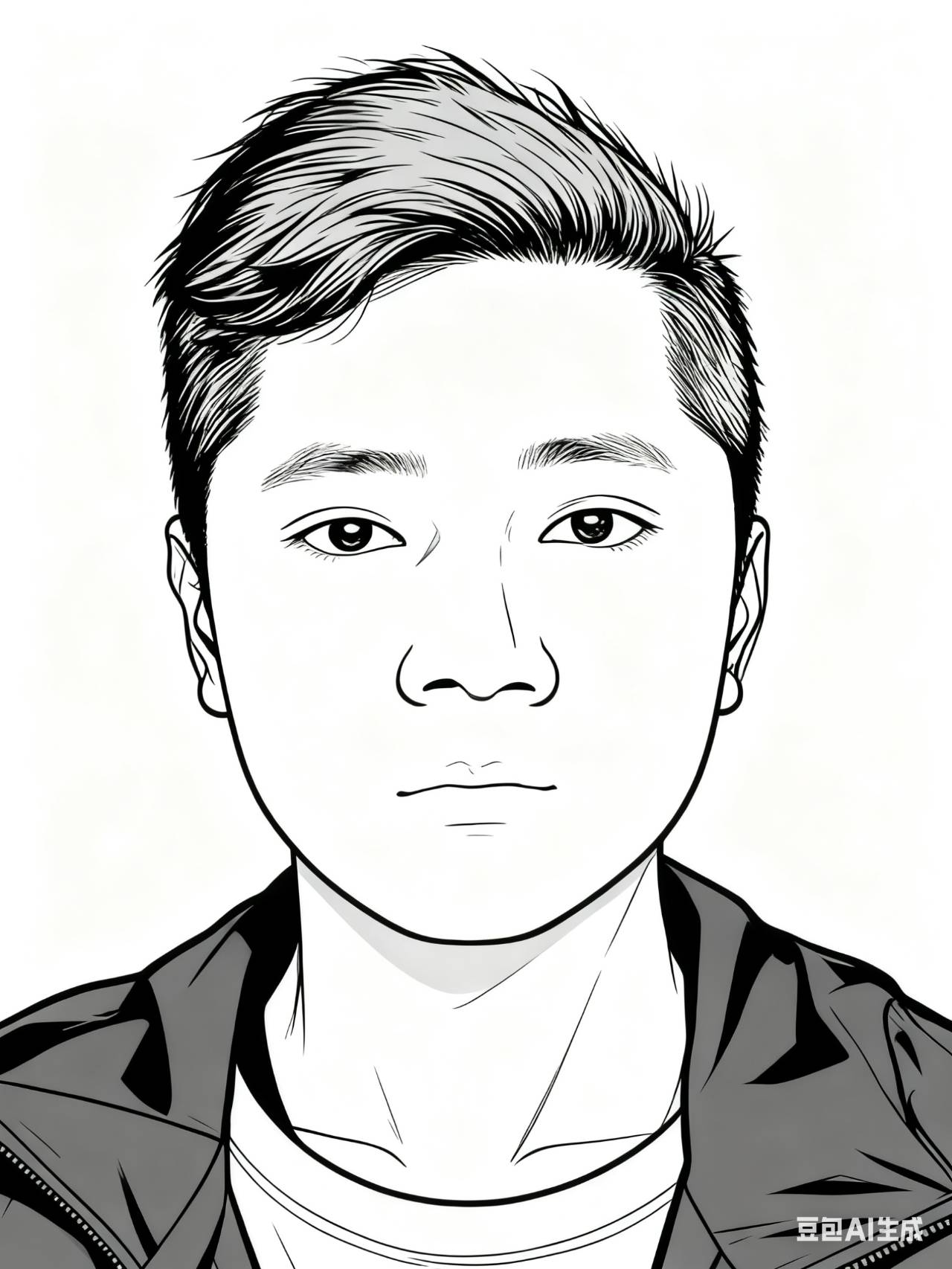
周末加班对小马哥而言已是常态,窗外的喧嚣与阳光都与他无关。就在笔尖即将落下修正的瞬间,脑海里却不合时宜地浮现出家的画面:刚满周岁的儿子,以及年事已高却仍在为他分担辛劳的父母。此刻,他们肯定又弯着已经不再挺拔的腰,在客厅里小心翼翼地护着、鼓励着那蹒跚学步的儿子吧。
那个小马哥错过了多次的温馨场景,像一根温柔的针,轻轻刺破了他因疲惫而有些麻木的心。他猛地甩了甩头,仿佛要将那份柔软的牵挂暂时甩开。下一刻,他不自觉地挺直了脊背,右手握笔的力道加重,在校样上划下更正符号的动作变得更快、更坚决。他必须再快一点,再专注一点。仿佛只要他在这里快一分钟,就能早一分钟推开家门,从父母手中接过那份甜蜜的负担,让自己的臂弯成为儿子探索世界时最坚实的依靠。
蓝笔在纸面上沙沙作响,那声音急促而密集,像是在追赶时间,也像是在为自己,为家人,奋力划出一道通往寻常烟火幸福的捷径。
小琴——
采编室里人声嘈杂,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像一片喧嚣的海,只有小琴的世界依然安静,她坐在小隔间里,仿佛自带一个无形的屏障,将周遭的纷扰都调低了音量。
发现样稿上的疑似错误时,小琴会不自觉地将脸凑近版面纸,左手食指的指尖缓慢而坚定地划过每一行字,如同最精密的探针在扫描大地深处的裂隙。右手则紧握着一支蓝笔,像握着一名沉默骑士的佩剑,不时在某个词、某个标点处停下来,画下一个又一个清晰的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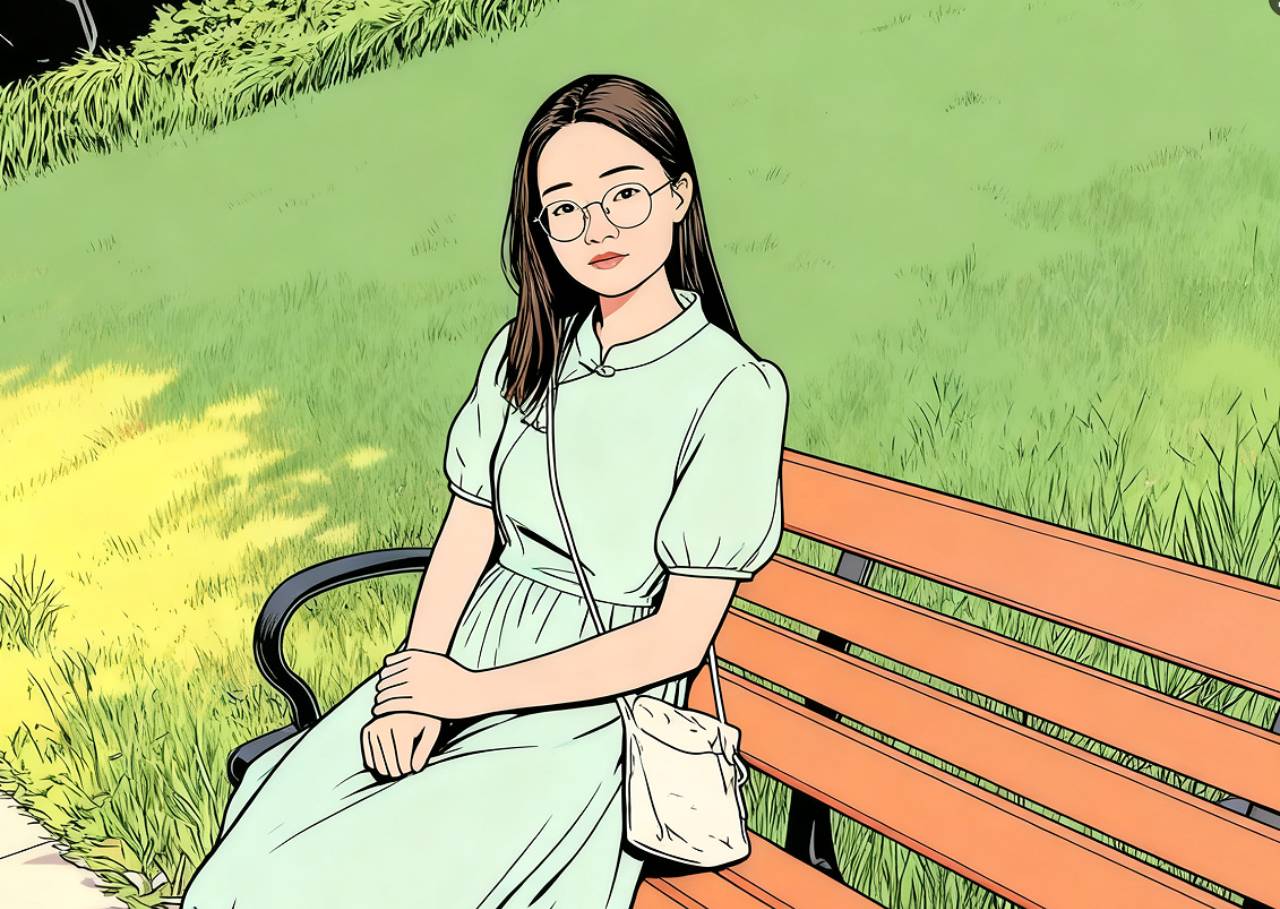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蓝色的墨水痕迹在光线下看起来格外显眼,那是一种沉静而深邃的蓝,不张扬,却无法忽视,像是沉入深海中难以被外界探测的秘密,只属于她一个人。
突然,耳边炸响起同事一句夸张的惊叹,大约是某条突发新闻或是某个趣闻。小琴握笔的手指顿了一下,连带着那安静的蓝色也似乎在纸上凝滞了一瞬。她抬起头,目光掠过隔间挡板,望了一眼那热闹的源头,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笑意太浅太淡,还未抵达唇边,便只在眼底漾开一圈浅浅的涟漪,旋即消散无踪。
小琴重新低下头,手中的蓝笔继续与纸张进行着那种心照不宣的、温柔的摩擦。“沙沙”的声音细微得几乎被环境的噪声吞没,却是她世界里最清晰的律动。她就这样耐心地注视着,审视着,守护着文字构成的那个喧嚣世界,并用一道冷静的蓝,为它划定清晰与规范的边界。
萍萍——
隔壁工位突然传来萍萍带着哭腔的抱怨:“这稿子咋改!第一句就没理通顺,作者到底要表达啥?”她盯着屏幕上那句结构拧巴的话,像在解一团被猫玩乱的毛线,越是想理清,缠得越紧。主语藏在层层叠叠的修饰后面,动词软弱无力得像没吃饱饭,根本找不到宾语在哪。标点更是随意洒落,可怜的逗号承担了所有停顿的职责,包括那些本该是句号郑重出场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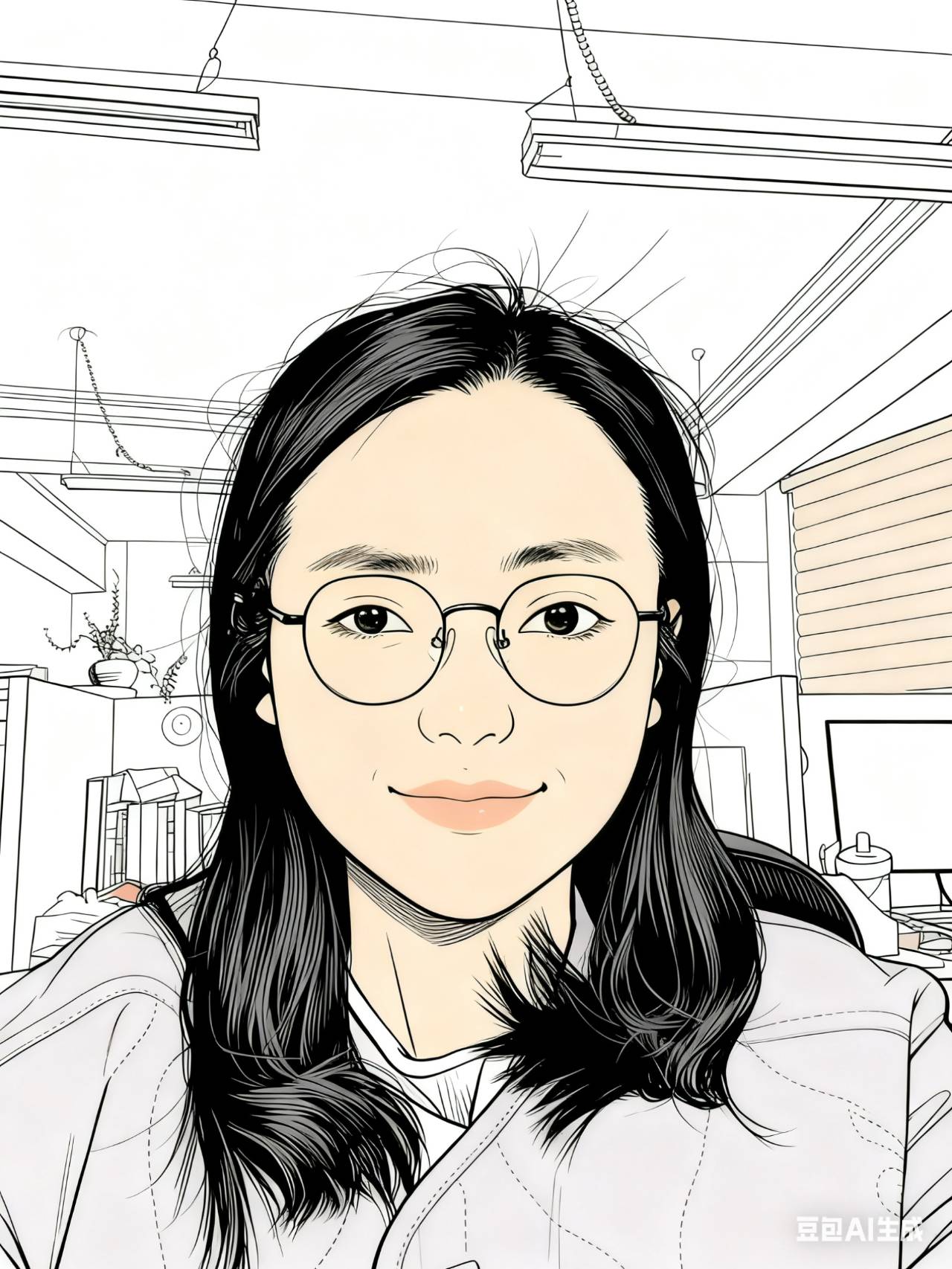
萍萍烦躁地揉了一把头发,还来不及为掌心那两根被自己无意薅下的发丝哀悼,手机铃声就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尖锐响起。听筒那头是部门主任不容置疑的声音:“领导刚指示,今天的4版整个撤换,全部上新稿,你手头那个先别校了,等新稿来。”
“好,知道了。”萍萍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她轻轻挂断电话,仿佛只是接了一个寻常通知。这一天的工作,再次从徒劳开始。她默默关掉了那个让她抓狂的文档窗口,没有保存。屏幕上闪烁的光标,像一声无声的叹息。
几乎是同时,整个采编室被一种新的、更急促的键盘敲击声淹没——那是所有编辑在接到换稿通知后,开始争分夺秒地重组新稿的声响。这声音此起彼伏,紧密得如同战地医院里,医生们正在给垂危的病人进行一场场紧急抢救手术。
而萍萍,只是熟练地打开了另一个文档,不知这个文档的手术会不会又是有始无终的开始……
周周——
月光早已悄然爬上她的书桌,像一摊清冷的、无人收拾的银箔。她点开了屏幕上标注着“待校报样”文件,红着眼眶与那些蜷缩在字句间隙的标点符号无声地对峙着。全角、半角! 这细微的差别,在她眼中如同鸿沟。正当她揉捏酸胀的眉心时,余光像最精密的探测器,猛地捕捉到了“帐号”二字。神经瞬间一凛,疲惫被一种职业性的警觉驱散。又是“帐”“账”不分!她几乎能想象到,若让这个错字溜出去,会被多少人嘲笑,留下一个不够专业的印记。

周周的指尖,早已习惯了在字里行间这片方寸之地巡逻,常年游走,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敏锐,捕捉每一个潜伏的错别字、每一处标点的误用。久而久之,那张原本生动的脸,灵动的表情逐渐褪色,仿佛被文字的尘埃覆盖,凝固成一种职业性的、略带苛责的皱眉。
这状态甚至入侵了她的睡眠。连做梦,都常常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红色三角符号(那是标记错误的符号)的追逐中惊醒——那些是白日里的错误痕迹,化作了梦魇。
手边的笔记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备注,是关于易错词的、是关于新规的、关于各类术语的……这是她与文字搏斗的战术手册。而偶尔瞥见的手机屏幕上,微信朋友圈里,同龄人正分享着山河远阔、美食与聚会,那些鲜活的、流动的生活,与她桌上每天增加的、永远也翻不完的、散发着油墨与纸张特有气味的校样,形成了一种无声而荒诞的对照。
她微微动了动僵硬的脖颈,“咔咔”作响,一阵熟悉的酸麻立刻传来。颈椎病和眼干燥症,成了她职业履历上两枚无声的、略带痛楚的勋章。她滴了眼药水,闭上眼感受那片刻的冰凉,然后,再次将目光投向那片文字的丛林,开始了又一次的狩猎。
兰兰和飞飞——
窗外阳光正好,兰兰和飞飞却挤在工位角落,像2只交换秘密的麻雀。“主任刚发的课件你们看了吗?”兰兰压低声音,“我越学越糊涂了……”“读书时觉得语法挺简单的,现在看校样,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像密码——我愣是没看出‘发现勿打电话’是病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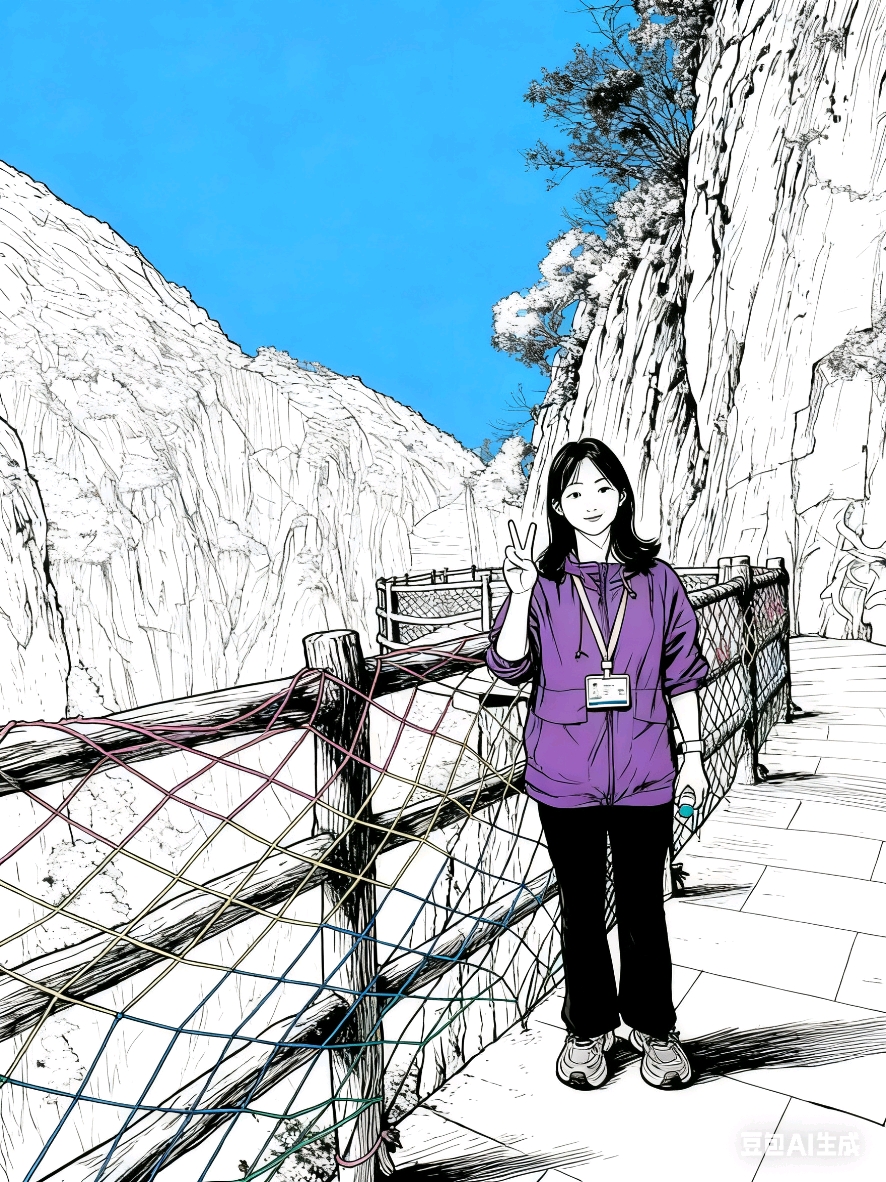
飞飞盯着笔记本屏幕上的课件,眼神放空:“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入错行了?我看崔老师改稿,蓝笔一圈就是一个错误,我盯着看3遍都发现不了问题。”

打印机嗡嗡作响,吐出还带着温度的校样。2个“新兵”相视苦笑,不约而同地伸手接过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入校对的江湖,他们还没练就火眼金睛,却在一次次怀疑与困惑中,磨砺着对文字的敬畏。
绮墨——
听到几个新人的窃窃私语,坐在角落的绮墨抬起头,放开清亮的嗓门说道:“多学多练就好啦!就像今天测试题里的‘闺蜜’和‘闺密’,你们都没发现问题吗?其实两者都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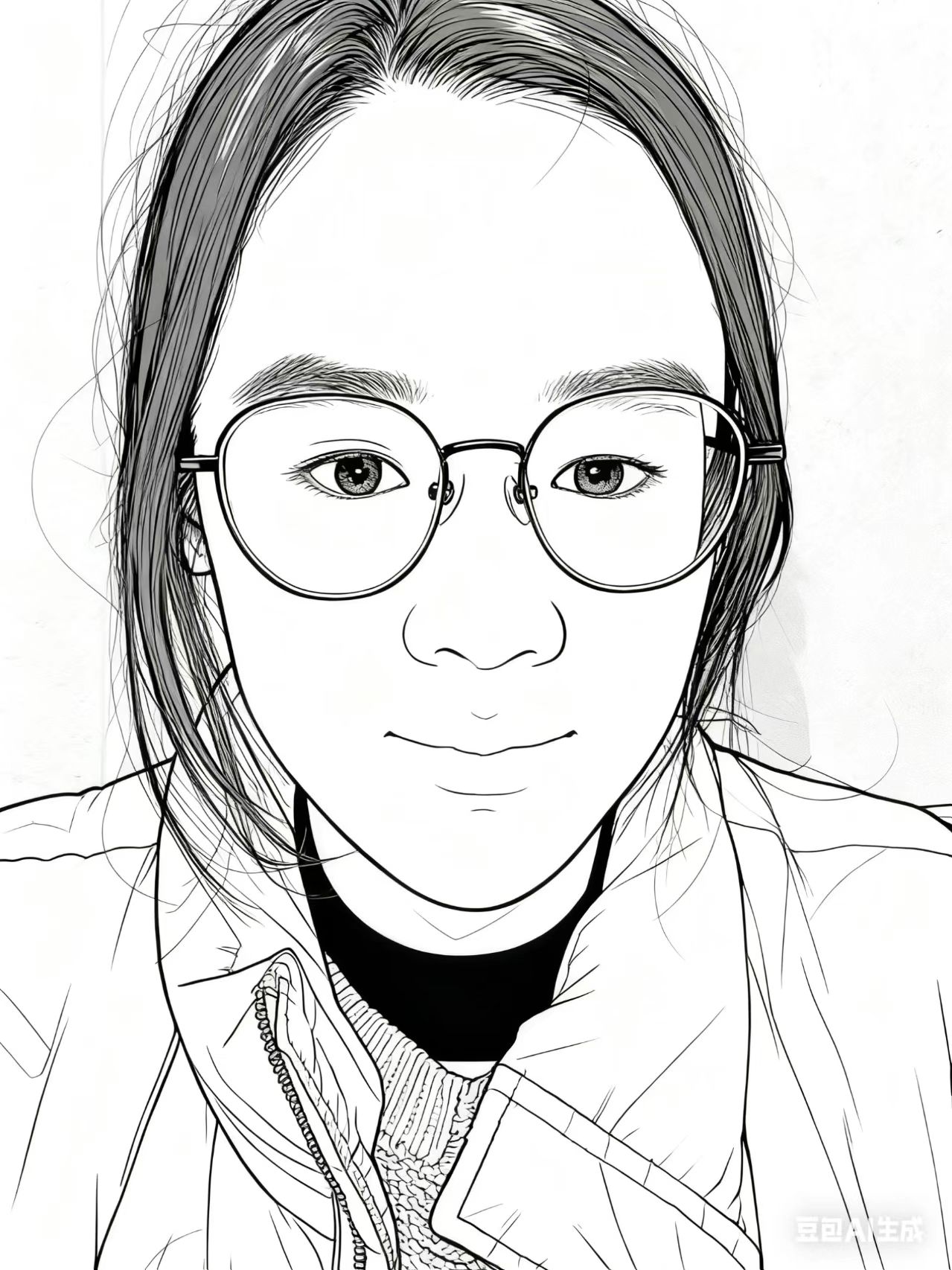
绮墨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闺蜜’是现在更通用的写法,口语化,也更常见;而‘闺密’呢,则更偏向书面表达,从字面上就更强调‘亲密无间’的意味。词典里两者都有收录,关键要看具体的语境和文体要求!”说到这儿,她熟练地拿起手边那本《现代汉语词典》,精准地翻到那一页,指尖“嗒”的一声点在那两行并排的释义上,动作利落得像一名出示关键证据的律师。
兰兰和飞飞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连测试题都会埋下这样的陷阱!区区一个常用词的选择,背后竟藏着如此细微的门道和深意。这不再是简单的对错判断题,而是在特定语境下对词义色彩和文体风格的精准拿捏。
校对工作的精密性,此刻像一道无声的惊雷,在他们心中炸开。它要求的不仅仅是对规则的死记硬背,更是一种对语言无限可能性的深刻体察,以及在方寸文字间寻求最恰当表达的极致追求。
松哥——
把两个闺女在校门口放下,看着她们蹦蹦跳跳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里,松哥便立刻调转车头,急匆匆地跨进了办公室。晨光才刚刚铺满窗台,电脑屏幕上,校对工作群的图标已经在闪烁,一篇待校的稿件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像一道准时的上岗通知。

又一天开始了,给文字站岗、给图片站岗、给视频站岗……他嘴角牵出一丝无奈的苦笑,滑动鼠标滚轮,屏幕上待处理的文档和链接如同永不消融的雪片,纷纷扬扬地涌来。他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明显后移的发际线,心里盘算着,老婆念叨的多吃黑芝麻、黑豆,也不知道到底管不管用。
视线回到屏幕上,密集的文字让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他想起医生反复地叮嘱——刚做完眼睛手术,要少用眼,多休息。他几乎没有犹豫,便移动鼠标,点击了打印。打印机开始发出熟悉的嗡鸣与吞吐声。他决定,还是将稿件打印在纸上,用笔来校。这既能护一下刚刚动过手术的眼睛,似乎也能在触摸纸张的实感中,找到一丝与冰冷屏幕对抗的慰藉。尽管他知道,这不过是杯水车薪的自我安慰,那如山的工作量,并不会因此减少分毫。
老王——
老王已在校对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7年,岁月似乎格外厚待他桌上的物件:那本《现代汉语词典》的书脊,被透明胶带反复缠绕、加固,如今胶带早已泛黄、斑驳,边缘卷起,如同古书的风霜痕迹;抽屉里静静躺着的几支英雄牌钢笔,笔帽与笔杆的接口处已被磨得光滑锃亮,露出了底下深藏的铜色,它们陪他走过了数十个春秋,每一道磨损都是一段与文字厮守的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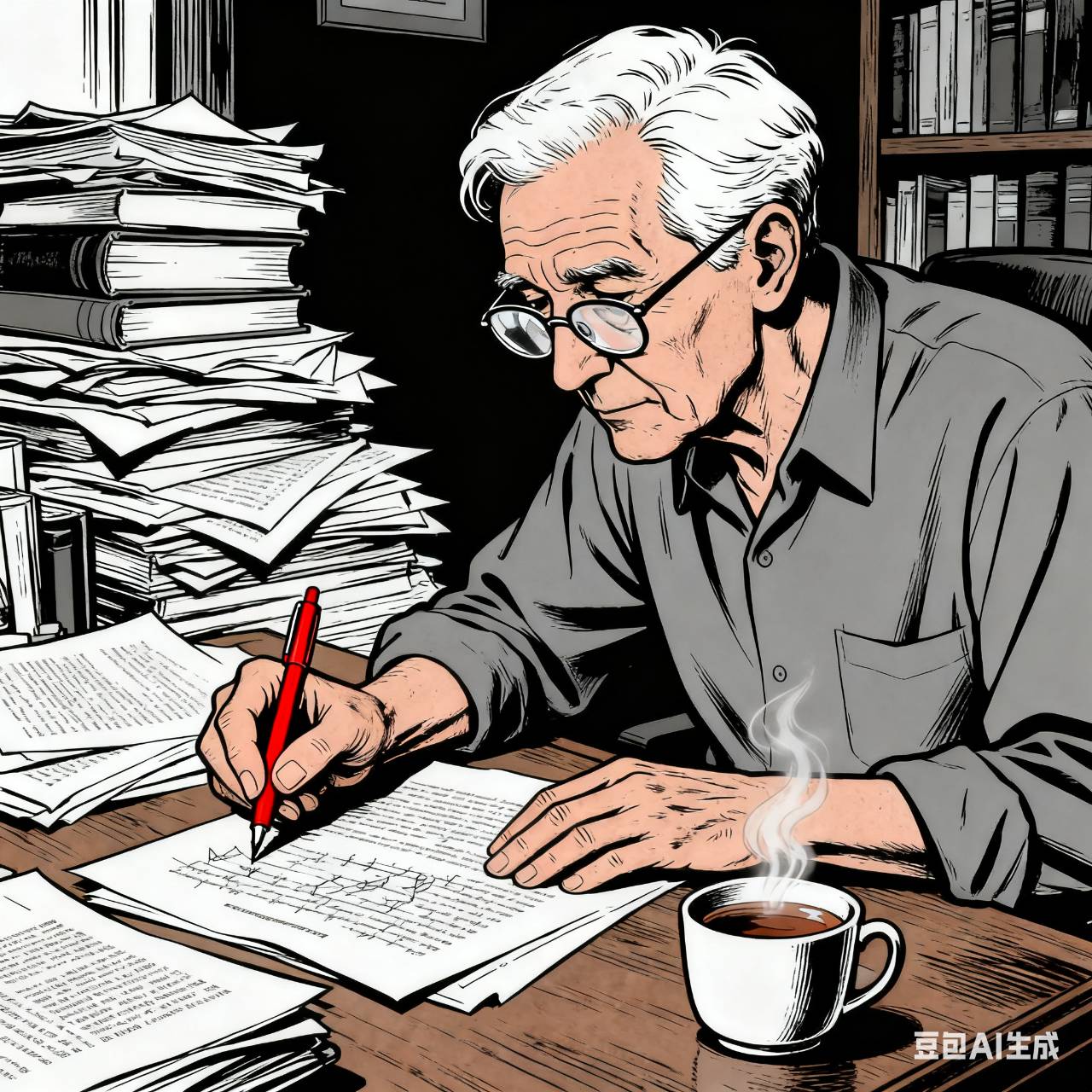
窗外,枯黄的树叶被深秋的寒风吹得“沙沙”作响,那声音连绵不绝,仿佛在窃窃私语,嘲笑着他对文字秩序近乎固执的、或许已是徒劳的坚守。然而,这外界的声响从未真正扰乱过他内心的秩序。他时常对年轻的校对员念叨,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文从字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点都不能含糊。”他会用那支磨损的英雄钢笔,轻轻敲击着桌上那本“饱经风霜”的词典,“你们要经常翻看字典、词典、《辞海》,要多学习,底子打好了,手上才有准头。”
他的话,不像是在提出建议,更像是在传递一份绵延了数十年的信念。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文字最初的严谨与体面。那斑驳的胶带与磨损的笔杆,便是他无声的勋章。
晓雨——
作为高学历的大才子,晓雨没入职前,觉得工作中没有什么问题是搞不定的,但现实的沟沟坎坎却让他崴了几次脚。他在工位上近乎无声地嘀咕:“我们对文字的徒劳坚守,有啥意义?记者不理解,编辑不理解……”这话轻得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深潭,只在意识的表面漾开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旋即被四周更加密集、更加实在的键盘敲击声彻底吞没,仿佛从未存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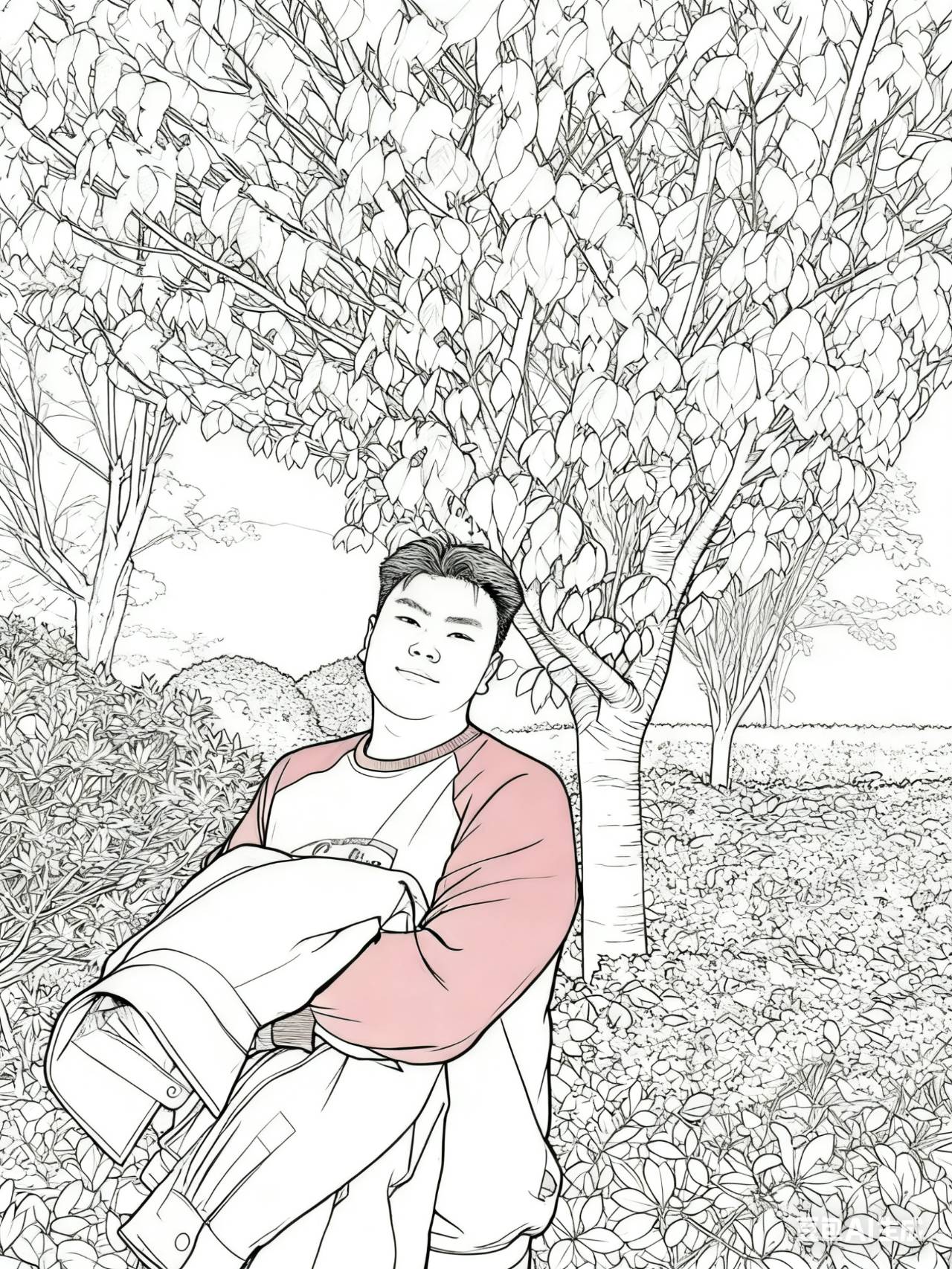
他面前摊开的校样上,蓝笔留下的轨迹细密如织,将文字的顺序一一归位,为误用的标点套上规范的缰绳,把那些漂浮不定的语意锚定在坚实的语法地基上。每一个标记,都是一次微小的、对抗混乱与模糊的无声战役。
这徒劳吗?他不禁想起刚入职时,部门主任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这岗位,首要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做好了,那是理所应当,没人会特意表扬;成绩和荣誉,似乎总是和我们隔着一层。但越是如此,越不能浮躁。记住,样稿上只要留有一个错,哪怕再小,到了读者眼里就是天大的事,白纸黑字,无可辩驳。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多学多问。”
主任的话言犹在耳,像一枚定海神针,暂时镇住了他心中翻涌的迷茫。他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那份浮躁从胸腔里挤压出去,随后再次握紧了那支蓝笔。笔尖落下,精准地圈出了下一个隐匿的标点错误。
在这个追逐速度与流量的时代,这种对精确的执着,或许显得笨拙而固执。但总得有人,在喧嚣过后,为那些即将成为白纸黑字的语言,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沉默的一次把关。
燕姐和梦姐——

燕姐和梦姐熟练地插上硬盘,文件夹里是刚寄来的片源,密密麻麻如一片待开垦的荒地。在旁人艳羡的追剧目光里,她们戴上眼镜,一个握住鼠标,一个摊开记录本,像两位即将步入雷区的工兵。快乐的追剧是沉浸故事,而她们的审片,则是将故事拆解成无数个需要证伪的零件。查演员,更像是一场人事排查。燕姐对着演员表,查找有没有污点艺人。这早已不是艺术欣赏,而是政治与风险筛查,她们不仅要记住那些赫然“落马”的,还要警惕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有一次,在几十个群演人堆里,一个“落马”的隐匿其中,那一刻的冷汗,远比任何恐怖片都来得真切。

盯字幕,是一场对规范的发动的战争。她们的视线必须像扫描仪,一行行掠过屏幕下方的文字。听配音,则是对听觉神经的极致折磨。她们需要屏蔽剧情的吸引力,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声音与文字的同步率上。口型对不上、台词与字幕有出入、不该有的停顿,甚至背景音里是否混入了不该有的杂音……都需要精准捕捉并记录时间。长时间的专注,常常让她们下班后,耳朵里还残留着各种声音的幻听。最让人精神紧绷的,是怕黑屏。突然的画面中断,哪怕只有0.5秒,都可能是事故。她们必须像守夜人一样,死死盯住屏幕的亮度,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两人都临近退休了,但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她们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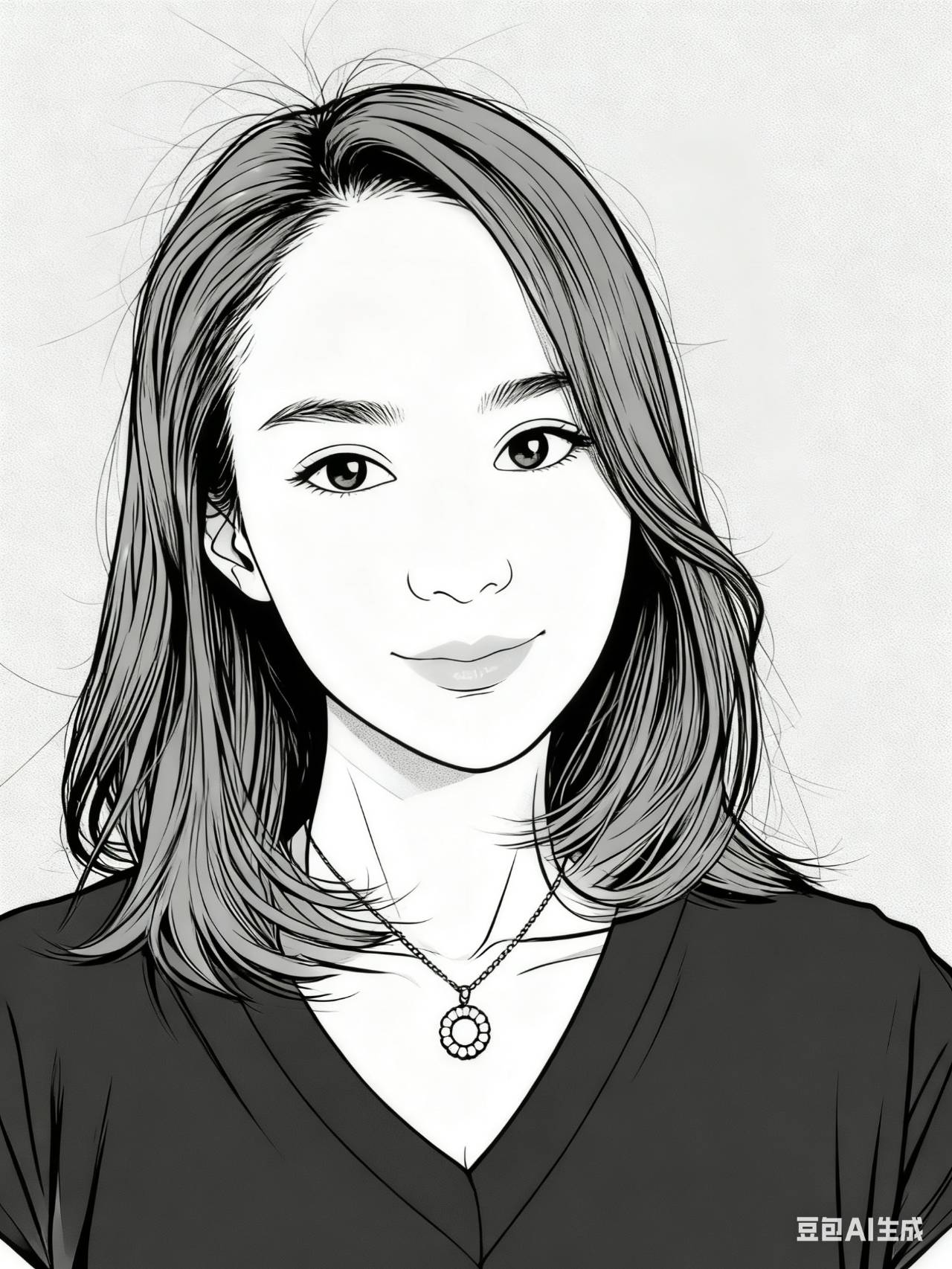
作为部室的门面担当,路路希望年轻的容颜永驻。梳妆台上摆满瓶瓶罐罐,她熟悉每款精华的黏稠度、面膜的服帖度,可每天面对电脑屏幕,那些精心护理的成果正被无声消磨。蓝光像细小的针,胶原蛋白在辐射中悄悄流逝。她明显感到皮肤更容易干燥,眼周细纹即使用最柔和的指腹按压也难以抚平——那是比任何审校错误都更顽固的“错别字”。但她还是会准时坐在电脑前,打开新的剧片,关注着台词与字幕有没有出入、转场还是黑屏……
雪儿——
雪儿独自一人守着平台,像一名哨兵守卫着最后的关口。“零差错”——这是平台铁一般的律令,也是悬在她头顶的剑。每一个标点、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称,都必须经过她目光的反复炙烤。她知道,在这里,99%的正确等于100%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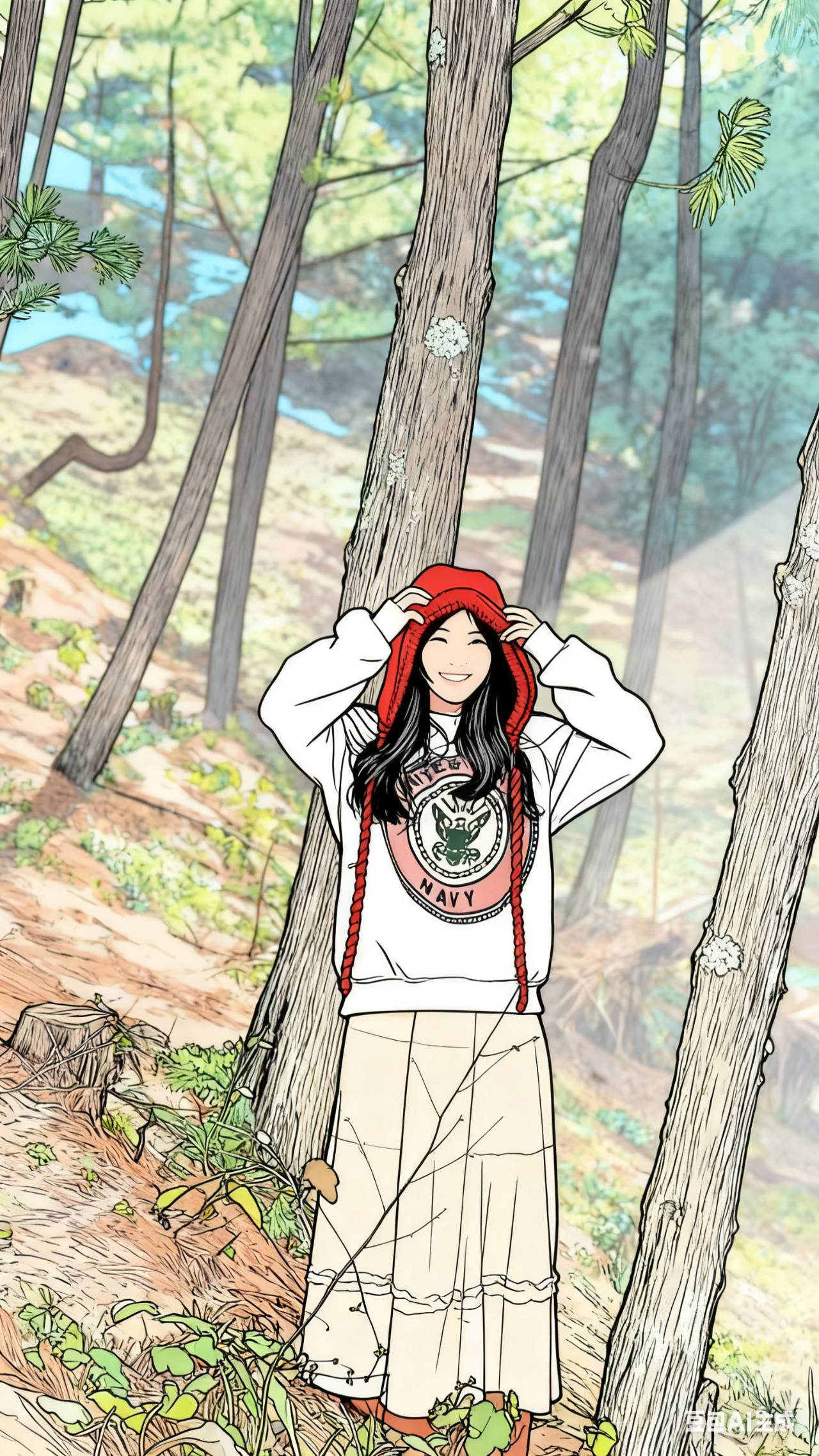
屏幕的光映着她的脸,指尖在键盘与鼠标间流转。她时而蹙眉查证,时而屏息核验。在这个信息奔流的时代,她的工作近乎一种“逆流”——用最慢的姿态对抗着最快的传播。当最后一条信息确认无误,她轻轻点击对话框回复编辑。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只有新一批待审内容悄然涌入列表。
她直了直腰,继续守在这片无声的战场上。零差错的背后,这幢大楼里还有十几个像她一样的守夜人,用专注与时间博弈,在信息的洪流中默默筑起一道透明的堤岸。
记者追逐事件的脉动,编辑构筑版面的骨骼,而他们是最后那层无声的薄膜,滤去所有毛躁与浑浊,只为换取一份清透与准确。这份近乎偏执的严谨,在求快求新的洪流里,显得如此笨拙,甚至迂阔,但他们愿世界无错。
记者:周燕/文 图片由AI生成
校对:胡远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