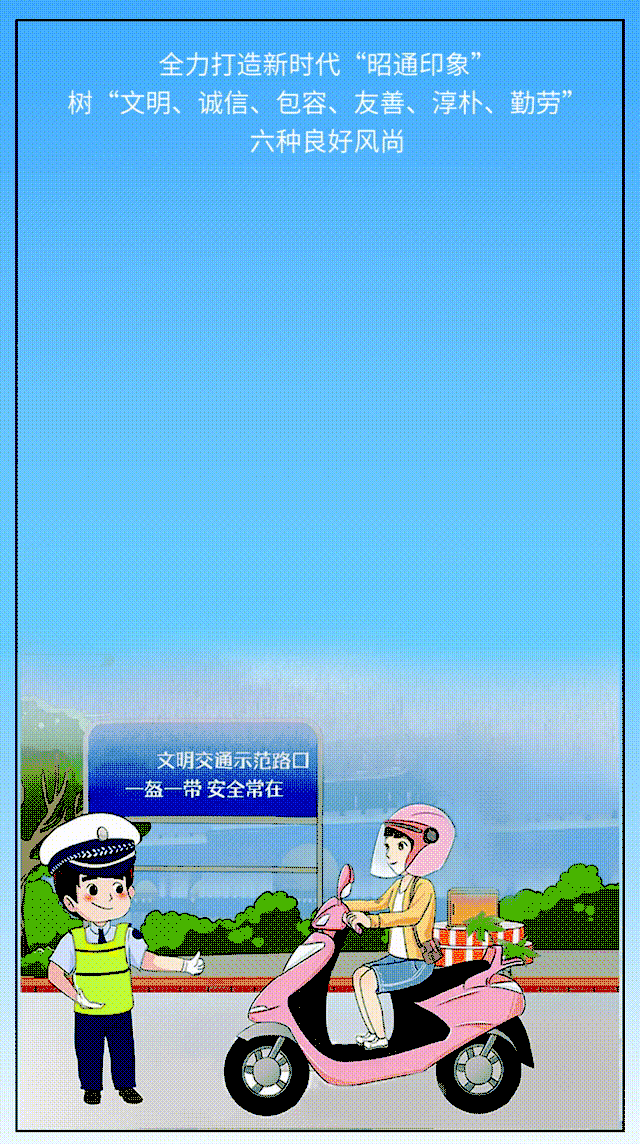2025-11-08 10:24 来源:昭通新闻网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酒桌从来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场所,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微缩的社交场域与权力剧场。新时代偏远地区的农村,一群“留守女人”的酒桌又藏着怎样的一片天地呢?
9月27日,我在昭通学院聆听专家们对《女人酒》一书的解读后,再次捧读此书,似品到了文中酒里的甘甜。
夏天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昭通本土作家,以《女人酒》独特的“留守女人”酒桌视角,透过女性与酒这一特殊介质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改革开放后女性意识的多维面向。在他的笔下,酒不再只是男性世界的附属品或情色想象的载体,而是成为女性表达自我、争取话语权、抱团扛起生活的液态媒介,成为一种流动的抵抗与重构之力。
长久以来,酒桌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中最为固化的场域之一。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男性通过敬酒、劝酒、划拳、干杯等一系列仪式化行为,将酒桌变为巩固联盟、展示权力层级的日常社交场域。而女性在这一空间中则常被客体化——或成为被观赏的“花瓶”,或沦为被劝酒的对象,其存在似乎只为衬托男性的主体地位。这种酒桌文化,实则是一种性别权力的展演机制,女性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交换之外,沦为男性社交中的装饰或牺牲品,是日常生活中极易被忽视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具象呈现。
而《女人酒》展现了留守在家的女性如何主动进入这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领地,并尝试重写游戏规则。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不再被动接受酒桌文化的安排,而是开始掌握饮酒的主动权。她们选择何时饮、与谁饮、饮多少——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更深一层,作品揭示出女性在酒桌这一特殊场域中如何保持自我意识的清醒:即便身体醉了,精神上却异常清醒地知道自身处境与目标。如刘菊喝醉后吐了爱干净的郑琼一身,郑琼却洒脱地坚持照顾她;王幺幺骚扰妇女后,女人们集体收拾他,打完之后见他挣扎跌倒,又一起搀扶他……这种“醉中的清醒”,正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隐喻:她们参与游戏,却不完全接受规则;身处权力结构,却试图从内部改变它。
小说中女性借酒实现的抵抗,本质上是一种“液态抵抗”。它没有固定形态,不采取正面冲突,而是如水一般渗透、流动、适应,在看似妥协的表象下实现自我表达。这种抵抗方式,体现出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智慧。她们并非要彻底推翻酒桌文化,而是要重新定义自己于其中的位置与角色,将酒桌从纯粹的男性权力场转变为性别互动的可能空间。
《女人酒》中女性意识的流动性,也体现在代际差异上。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对酒的态度、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别,反映出女性意识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演变。年长一代或许更倾向于借酒维系家庭关系,中年一代可能将饮酒视为职场生存策略,而年轻一代则更愿将其看作个人自由的表达。这种代际差异并非简单的线性进步,而是展现了女性意识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复杂适应与重构过程。
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女人酒》揭示了当代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虽然女性已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公共领域,但许多传统的社会规则与评价标准仍由男性主导。正如20多年前,周家庄暮春插秧放水时,男人扛着洋铲、板锄抢水的场面——谁家男丁多,谁便是赢家。而今天,“留守女人”不得不在遵循现有规则与挑战规则之间寻找平衡。酒桌只是这一困境的缩影——女性或可借掌握酒桌技巧获得一时成功,但这究竟是改变了性别权力结构,还是仅仅成为游戏中的高手?作品并未简单给出答案,而是留下这一深刻的悖论,引人深思。
《女人酒》中,当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沿海城市打工,我们关注的更多是留守儿童如何健康成长,却常常忽略“农村人家,家家都有难处,家家都有心酸的、难以言喻的事”。这些痛,深深触动着“留守女人”的心。在扛起生活的艰难岁月里,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一个渐进而充满矛盾的过程,更成为一种革命。她们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不断调整身份与位置。她们对酒的态度变化,实则是自我价值认知的变化——从完全排斥酒桌文化,到策略性利用,再到试图重新定义它,这一过程正反映出女性意识从觉醒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夏老并未将女性饮酒简单地化为女性解放的标志。他清醒地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女性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也可能陷入新的困境;在挑战一种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刻板印象。这种不简化现实的态度,使作品对女性意识的探讨更具深度与真实性。
《女人酒》中展现的就是最终指向一种新的人际伦理与性别关系的可能。当女性不再是酒桌上的客体,当饮酒不再是男性特权的象征,当敬酒与饮酒成为一种平等交流而非权力展演的方式,我们或许能期待一种更真诚的性别互动方式的诞生。书中和善内向、人缘好的淑芬,借酒排遣内心积怨,把受人排斥的刘菊约来喝酒,又以酒为媒化解刘菊与郑琼之间的矛盾。正是通过这种女性“约酒”的新酒礼,改变了传统男性酒桌上“谁喝倒谁谁就是大哥”的陋俗,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时的尊重与理解。
自古以来,中国的“酒”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变迁中女性意识的流动与重构。夏老在《女人酒》中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这种液态抵抗的瞬间,记录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
淑芬说:“跪什么跪,男人脚下有黄金,女人脚下也有黄金。”而在“约酒”之后,她们吐了苦水,也吐了“肚里的秽物”,“毫无顾忌”地哭过之后,“留守女人”终于放松下来,言语间也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从容,都认为“洪水过后,云消雾散,一切又从头开始……”
这些在酒液中流动的女性意识,或许正是解读传统性别秩序、建构新型伦理的起点。正如《红楼梦》所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女人本就该有水之灵秀,既具不卑不亢之温柔,亦含灵动婉约之睿智。“遇石而绕,入渠而顺”,择可行之路,从容自若,悠悠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女人酒》不仅是一部关于女性与酒的作品,还是一部关于自由与尊严的现实寓言。它就像是平凡生活中用心酿成的老酒,越品越有味。
作者:马伯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