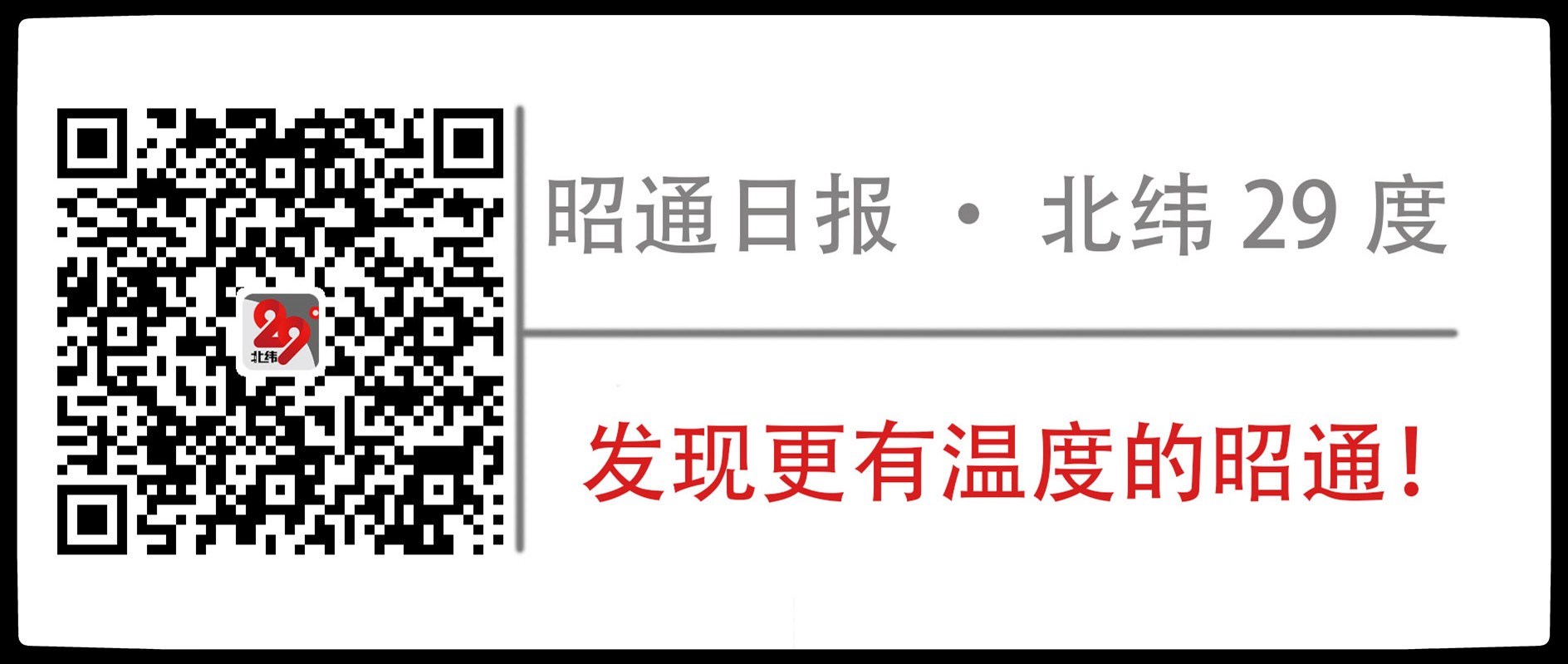年会唤醒世间的颜色和气味。时间表,路线图,都十分清晰。现在,只要进入冬季,我就会忆起过年的场景。我以为年对于人类,永远是一种“情结”。
年的色彩和快乐,忙碌和充实,十分具体。过年的时候,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内心都会觉得已经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记得小时候,进入腊月我就开始激动起来。尽管大人常说“腊七腊八,冻死鸡鸭”。说明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可也是作为孩子的我们最有热情的时候。因为年的气象、氛围,各种平时少见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仿佛一年中的会展:杀猪,卖春联、年画,卖山上的杜鹃花,还有各种吃的,葵花籽、叮叮糖、麦芽糖、籽糖、苞谷糖、爆米花等等,过年真好!年不仅孕育万物的风雨和泥土,还储藏人世的传承与理想。腊月二十四必须掸尘,原本是一场大扫除,却不叫扫,叫掸。轻轻地,把尘灰掸掉;墙壁要么粉刷,要么用画报、报纸裱糊。在除夕那一天,把该洗的洗净,穿上整洁的衣服。
人与物,都上下一新。
这是对一年时光尘封的收拾。收拾结束,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的成果,欣赏着新新鲜鲜的场景,仿佛所要获得的,基本已经实现。于一个渐渐长大的孩子来说,一生的理想都达到了,是幸福,是甜蜜。过年,虽然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并没有被财富的多寡左右。年就是希望,希望永远是人活着的动力。年过了,又带着希望去生活。然后,在第二年里,又想着实现理想。一年又一年,年在消失,又在重生。时间在连续,人在连续的时间里不断实现一生的理想。年的风景,也就成了人的风景。或者说,历史也就是这么延续的。
人与万物,没有距离。近邻或者兄弟,虽共同生存在一个家园里,却有许多讲究。比如在饭前,每家人要先在土地庙、天井里、火灶前、供桌处敬神、祭先祖。上香,点烛,磕头如捣蒜,一点也不能浮皮潦草,那是生命本义的分裂与连续。或许只要呼唤的那个称呼或者名字还在,他们似乎就永远没有离开。他们在头顶上,成为生活中的守护神,护佑平安,护佑吉祥和如意。一切仪式完毕,还要用鸡蛋大的沙石放在火里烧红,再用火钳夹进用柏枝垫好的碗里,用水加醋泼上去,从屋子的每个角落到畜圈转一圈,雾气上升。这在我的家乡称为打醋炭,寓意来年清清静静、无灾无难。这些行为,赋予人心以爱和敬畏。看不见生命,却有灵魂。
新鲜、好奇。于孩子而言,那是最美好的一天。大人做什么,小孩都要去凑热闹,即便惹了麻烦,大人也只说“你走开,这不是你做的事”。不骂,也不发火,更不会动手。一点不会像平日里,不是被细条子抽在屁股上,就是被骂得狗血淋头。如果家里有隔辈的女老人,那天都会做针线活,兼顾照看小孩子。她们用各种方法,让小孩子待在旁边听故事。我外婆,一个小脚老人,在我家过了几个年,但总是重复同一个故事。生活的经验,常识和传说,也悄无声息地传入了孩子们的灵魂。所以,那时的大人孩子,知书不多,却很达理。
年饭就有很多考究。饭是要用木甑子蒸的,要满。舀饭时,要从边上顺着刮,中间是不允许动的,最后留下一个尖顶。寓示来年粮食像小山一样,接通了天上的灵气。菜要丰富,摆放在青松毛上。蔬菜是不用刀切的,蒜苗一棵一棵地煮出来,白菜青菜要用手撕成长条,叫吃长菜,寓意一年四季不缺菜。开饭后,大人会最先夹起一个骨头,啃下肉,然后丢进火里烧。烟火味弥漫,让一年到头都可以闻到肉香。吃了三碗饭后,才能喝汤,大人说能免遭雨淋。这种说法不知有何依据,是否准确,我没证实过。但是这一晚所有的话都是算数的,谁也不会去触碰这些民间的规则。很好的是,年夜饭,大人孩子都可饮酒。我似乎天生不善饮酒,喝5分钱一瓶的小香槟也会醉倒。小香槟消失很多年了,大概也就四五度吧,还带着甜味。后来我想,酒不醉人,是肉醉人。
那时的人都是馋的,有馋的本能和机会。
当时乡间也不知怎么会有“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说法。怎么会单单是老婆馋呢?人人都馋,都想吃到好的食物,想吃到平日里舍不得或者无法吃到的甜蜜。人人都有口福,吃得酣畅淋漓,在馋中得到了所有快乐和幸福。为了馋,即使在晚上睡前,也要把脚洗得认真。因为大人说,脚洗得干干净净,走亲串戚才有运气吃到肉。这一点,大概是教育人要讲卫生的意思。人人都把脚洗得白白净净,心里难道不也是为了馋?
过年的日子,承担着职责和使命。从除夕到初三,丧气话是不能说的。所有要从口里冒出来的话,全都要挑着吉利的讲。做事也一样,图的都是吉利、祝福、期盼和美好。从贴对联开始,内容都充满了喜庆。那时家家户户张贴的对联,不外乎是:欢炮声声报喜,红联对对迎春;国泰民安一岁胜一岁,人寿年丰一年强一年等。横批是:大地回春,紫气东来,招财进宝,吉祥如意或者五谷丰登之类。这些内容,似乎贴出来就装进了人们心里,红红火火的日子即将到来。是的,连晚上的灯,也不能像平日那样关闭。那一晚要灯火通明,光亮四射。火塘也不能像平常一样,要烧得更旺,更红火。初一这一天,不动刀。菜刀、剪刀、指甲刀,带“刀”字的东西都不碰。街上也不开市,即便有商店的人家,经营也只是开一个小窗口。大多卖东西的是地摊,虽然看得多买得少,街上却是很热闹。无论天冷天热,都是人挤人。当然,更多的是年轻人。街上会有耍猴戏的,表演魔术和气功的,卖狗皮膏药的……但是,只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小媳妇往哪里站,小伙子就会跟着往哪里挤。有时丢个火炮过去吓一吓,有时故意一个追一个以不注意的方式跑过去碰撞一下。如果哪个小伙看某个姑娘如意,又打听不到在哪里住,即便被冷北风吹得鼻子耳朵满脸通红,也会等着她回家。然后,悄悄跟在后面摸清她家住在哪里,打听到姓甚名谁,慢慢托亲朋好友前去提亲。
当然,那时最快乐的,应该还是孩子。每个孩子都可以坦荡直率地面对事物本身,欣喜的是穿上一件新衣服,更欣喜的是,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钱装在自己兜里。大人似乎没有孩子乐意,有句俗语说“农民怕过年,过完年就下田”。年过了,就要开始一年的春耕。但是,真的下了地,干活是不会偷懒的,人人都很卖力。事实上,大人也喜欢过年,所谓年,就是把所有的朴实和原质,在这个节气里,相互传递,以此消除人们心中的功利主义。然后,在那一天,觉得实现了自己对一个家的理想。只是现在,孩子基本远离了天然的集体主义,一些东西在逐渐淡化和消失。但是,年还是把绝大多数人带回到母亲身边。 作者 朱 镛
作者 朱 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