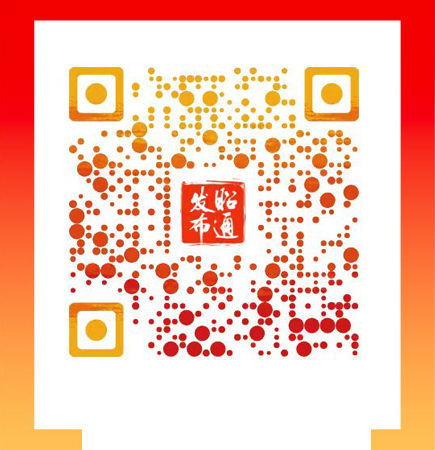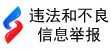小 果
小果村位于大理白族自洱源县城至茈碧老线3公里处,村民依坝子西缘山脚而居。现今,50余户200多人居住在一块向阳的坡地上,从村头至村尾,延伸出大约400米。据村子背后的坟山墓志可知,村民大都为明洪武年间自南京应天府迁居而来。汉族白族杂居,民风淳厚,古树弥天,整个村落似一片小森林,终年翠团环抱。
村民多以种植业为主,辅以林果和农牧。村落的得名,乃是因为村民房前屋后或村后的坡地林地之中,均种有大量的木瓜、花红、苹果、石榴、桃子、李子、梅子、杏子、柿子、梨、无花果、香橼、佛手、柑橘,还有核桃、板栗、花椒、山楂,一年四季弥散着浓浓的果香。
时光如逝,小果村早已成了一个虚无的名字。除了随处可见的木瓜和庭院内外尚存的花红、梅果,几十年前那么多种类的果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影。当然,类似这样虚无的村名数不胜数,比如大树庄没有大树,石桥村没有石桥,桃花村没有桃树,打铁营里找不出一户铁匠,赶羊涧村没有了赶羊的小道,换之而来的却是一条条高速公路……
小果村村民之所以为这个村名而自豪,那是因为村落之中还留有四五株树龄超过八九百年的参天巨树,学名黄连木,当地人称之为大漆树。每到春天,树枝上便结出一串串小果子似的花蕾,村里一首民歌开头一句便这样唱道:“千年大树结小果。”因此,村民以为村落的得名,乃是因为这几株黄连木,以为村落的历史和这几株古树一样悠久。
在小果村后的半坡之中,还有一个叫“花果山”的果园,至今还留有大量的老梨树、老核桃树和老柿子树,芳草萋萋、树木阴翳,仿若隔世桃源。据说“花果山”自古即有之,村民出工出劳,种药养茶,培育大量果木,每年所得收入充入公益基金,用于修桥造路、兴学办校等。位于滇西群山腹地的洱源县,属于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冬春偏寒少雨,每年大地春回之时,村后的花果山一派勃勃生机,时有游人前来露营观光。记得有一次,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骑着自行车,提着录音机戴着旅游帽,来到村口,也不下车,开口便向石岗上一位纳凉的老头问路:“哎,‘花果山’的路怎么走?”老头也不回答,侧身往后一指,几个学生便顺着老头的指引穿过村庄,沿着村后经常不见阳光的牛马道上山,泥泞路滑,行至难处,只得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感觉“花果山”近在眼前,却总到不了。无路可走之时,才想起问路时有些趾高气扬,只得有礼有节地向地里耕种的农人问路,才知道他们要去的是隔得不远、交通方便的龙泉公园。如此一番折腾,外人方才知道小果村后山路何等艰险,村民生计何等艰辛。
南沟边
村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除了一个被巨树掩映的古旧村盘外,小果村还有大量的山地、林地和耕地,不仅丰富了村落的内涵,还成为小果村物产丰饶的象征。
小果村的耕地分为旱地和水田。旱地分布在村落背后的坡头箐底,不知多少年前,就被辛勤的村民修整为阶梯状,一直伸延到入云的山间。因水利不畅,村民多种以果木,同时种上不需要时时灌水的作物,如洋芋、芋头、玉米、小麦、大蒜、油菜、百合、蚕豆、黄豆、豌豆等。水田主要分布在平坦的坝子里。古时,往往以一块田地是否可以种植水稻作为衡量土地价值的标准,小果村也是这样。几块为数不多的水田,分布在南沟边、小沟哈(小沟旁边)、水田坝、四田坝,是村落最重要的粮仓。
在这几块水田地中,只有南沟边是平平整整、方方正正的。南沟边面积宽广,从古至今都是小果村最核心的耕作地。南沟边面积大约300亩,因为水利和交通的优势,粮食的出产量大约占全村产量的六成以上。考究这块耕地的得名,兴许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南沟边夹在村子和往东大约500米的下小果之间,一条河沟从地块南缘流过,一直流经下小果村南头,成了村子与南边村落的界线,同时也成就了这个地名。
南沟边又被称为土山神。那是因为有一座小土丘兀立于这片耕地的西北边缘,整块耕地极为平整,中间地带略有些低陷,如点将台一般格外醒目,人们便称之为土山神。小土丘边有两户杂姓人家,据说是早年政府安置的外地人。他们初来小果村时连地都没有,于是,各家各户从田头地角分出一小块地,作为他们的口粮田。在南沟边坝子,每家每户的地都是大田,人口多的一块田差不多有两三亩。杂姓人家的田却如同拼图一般,细细碎碎,沿着水沟排列。很多年后,当我知道这些渊源,着实为村民当年的慷慨感叹,因为小果村的耕地并非多得种不完。
我家的两块水田就在土山神边。水田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一年四季,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大量的时间“泡”在这里。从四五月份把秧苗栽入地里开始,接着要补水、修埂、薅苗、割稗、赶雀、追肥、喷药、割谷、种豆、拔草、收豆、犁地、耙地、放水、复栽……然而,小时候我却十分害怕从土山神边路过。据说,有一家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夭折了,没有地安葬,就被大人连夜葬在了土山神中。后来我向他的两个哥哥问过这事,他俩哈哈一笑,说这怎么可能?葬这里不被野狗给刨了?早被大人葬到山后的义地里去了。说完还怕我不相信,兄弟俩抡起锄头,三下五除二就把土山神给掘平了,果然没有葬过人的迹象。
我一直觉得,土山神同样也是小果村和谐的象征。人们却将这块地改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是因为顺着南沟修了一条直通到县城的机耕路,而且也习惯了南沟边这个称谓。
寺
现今的小果村仅留下一座寺庙,即村子正中古树弥盖下的华严庵。庵内正西的大殿里塑有释迦牟尼、弥勒佛和观音之像,旁边的耳房里则有土地和财神。几十年来,门口的对联几乎全是那样:山神保佑山中客,土地扶持土上人。横批:有求必应。北房正中供奉的是手执长卷的孔子,慈眉善目,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每年孔子诞辰,村民都要在这里集会共祭孔子。包括其他各个节庆,这里绝对是村子里最神圣的地方,莲池会的老人要在这里诵经祈福,村民们要在这里磕头求安。香烟环绕,钟磬和响,整齐的诵经声如同唱诗一般,让古寺极富古韵。
在小果村,寺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位词。因为村落四周,就有许多地块因寺得名。比如“寺门口”“寺后头”,还比如村南的一块梯地被称作“寺南”,村子北上角的一块坡地被称作“寺北”,寺北斜上方又有一块坡地被称作“上寺门口”。村里的老人说,早年村子上头的确还有一座寺庙叫上寺,不知什么时候毁坏了,但几个代表方位和地名的农耕地却因此保留了下来。
历数小果的耕地或林地,有的从名字上就能确定地的用途。比如水田坝、秧田坝、竹园、花果山、苹果园、桃子园,但还有许多地块指示不明,如寺南、寺北、上寺门口等,村民们有时将其用作秧田,有时作为旱地,但更多的时候,是将之作为蔬菜地使用。
因几块地就在村落附近,很多人的劳动都是从这些地块开始的。小时候,我常会跟着姐姐们,挎上小篮子到寺北给猪牛割一篮草,或到寺南自家地里代父母浇地。春荒二三月,小果村也常陷入水荒,大半夜里挖不到水,地总是浇不透,人只能站在埂上干着急,我也曾悄悄把水源上游几块秧田的水坝掘开,让积水流到我家地里。但这样的“勾当”很快就被人发现了,秧田主人指着我家地里的浮萍指桑骂槐,害得我很长时间不敢从他家门口经过。
更多的时候,我会跟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和父母一起伏在地里精耕细作。初夏的蒜地板结,固如坚冰,我们找来水源,浇在上面,趁着有湿气用条锄挖开泥土,再将蒜苗一棵一棵拔出来。但水不能浇得太透,否则人在蒜地里就如踩烂泥一般深陷其中;若是浇不透,蒜又拔不出来。在泥土里长了一季的蒜瓣,像极了这块土地上人的脾性:宁为“蒜”碎,不为瓦全。纵使你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蒜叶拔脱,把蒜秆拔断,也休想将蒜拔出来。最终只能拿来条锄,使足力气再刨个坑,才能将早已碎散的蒜瓣刨出地面。蒜碎了,就没有了卖相,可不挖出来,却又影响下一季的耕作,因为它依旧会在地里生长,夺走玉米的养分。
有时,我也会跟着父亲在玉米地里培土。烈日当空,人们头昏眼花,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直不起身。待到晚间休息时,脸上臂上手上脖子上,全是玉米叶划出的细口,又辣又痛,浑身上下就像被人毒打了一顿似的。冬日严寒到来,我还会陪着父母到山箐里挖百合。那些常年少阳光的箐地,山风一阵紧接一阵,从山头急疾而过,吹散的泥灰就如同雨点一般往人身上浇,有时让人睁不开眼睛,有时让人满身都是灰。大人抡起锄头挖开了百合墒,我们就跟着弯下腰如同捉虫一般,把百合一粒一粒“捉”进箩子里,顺手抹掉泥巴掐掉根须,按大小归类。一天下来,我们用10个指头将一畦泥土一把一把翻碎,身子常常如深陷冰窖一般。
我确信,小果村背后一块块鱼鳞状的大小梯地,珍藏着一代代村民最辛勤的汗水,同样珍藏着历代村民对土地的忠诚和热爱。
牛滚塘
牛滚塘位于小果村后山之中。据说几十年前,这里是一片高山草甸,绿树成荫,飘岚走雾,水草丰美,有大量的牛群出没,牛滚塘因此得名。
一年到头,村民们在这附近的山地摞松毛、捡松球、砍松柴、采松脂、割茅草、拾菌子、挖草药。从牛滚塘发源的一溪箐水,流经汽早涧、汽早坡、回下登、竹园、秧田坝,最终从寺南流过,沿途滋青吞绿,与花果山背后的龙水,成为村落最重要的两大灌溉水源。
几十年前,村民们竟将牛滚塘附近几个山头的大树小树砍伐一空,甚至连树根都一块儿刨走,妄图把梯地一直修到与天齐平的山巅。令人惋惜的是,牛滚塘消失不见了。从此,村民们砍柴拾菌得多走十几里路,到达后山背后的石照壁,甚至是更远的罗坪山腹地。让老辈人至今谈之色变的是,有一个夜晚突降大雨,村落后山发起了大水,差点将整个村子淹没。
植树造林很快成了村落的一大主题。几十年后,小果村后山又被葱郁的松树覆盖,人们又可以在其间牧牛采菌了,但牛滚塘和水塘沿途的好几口井,却成了一个永久的传说。
阿荣坡坡
小果村与后山之间,有一条回环的山路,沿途连通了秧田坝、竹园、回下登、汽早涧、汽早坡、赤登间、花果山等一系列坡地、箐地和山地,后山却不是终点,因为后山的背后是石照壁和石门槛,过了石照壁和石门槛,路继续向前伸延,最终消失在了起伏连绵的罗坪山中。
如果把村落当作起点,那么从出村至秧田坝一段,还较为平缓。但百米过后,前面便出现了一个急坡,村民称之为阿荣坡坡。水从坡上往下流,狭窄的坡路就在沟边伸延。路是土路,土是黏土,下雨的时候,路就变得异常湿滑,牛走到这里,差不多都不用走路,只需定定地站着,便能顺着坡稳稳地滑下来。
这是小果村里为数不多的以人命名的地点。大人们说,阿荣是村里的一位老人,已经去世50多年了。据说,早年政府鼓励村民垦荒造田,多打粮食,但别人垦的荒都成了私田,种上几蓬刺篱笆,就把上百亩的山地、坡地据为己有。有的种上树,有的种了粮食,有的盖上房子成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家园,还有的什么都不种,就让一大块地荒着,只有阿荣坡坡成了村里的公路。古往今来,村子里老老少少逝去那么多人,只有阿荣至今还念在人们嘴里。
花石坡
花石坡位于牛滚塘后山,两者相距大约500米。远远看去,只见一面树木葱郁的山坡上,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如同飘带系在山腰。小路上面,有一块硕大的花白石头,如同美玉一般被衔在山腹之中,异常夺目,这就是小果村地界的终点。
对于小果村而言,花石坡还有一个美妙的传说。据村里的老人讲,早年罗坪山中常有山匪出没,抢劫山下的村庄,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一天,一帮匪徒决定抢劫山下的小果村,哪知刚行至山中的花石坡,便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电闪雷鸣、大雾弥漫,连面对面都看不清谁是谁,匪徒只能躲进山坡中避雨。好不容易大雨停了,大队人马一路马不停蹄,浩浩荡荡杀入小果村中,却发现整个村子一片死寂,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一点生机。匪徒心中疑惑,撞开几户人家,却发现房子里空空的,连谷仓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最终人困马乏,匪徒只能悻悻离开。半年后,匪徒旧计复施,半山之中又遇到暴雨,同样只剩一个空村。
匪首心中疑惑,便令手下化装后潜入村中暗中侦察。每当匪徒行至花石坡,罗坪山瞬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倏然而至。来势汹汹的土匪只得躲进密密匝匝的松林中避雨,锐气大挫。而村民们收拾好粮食细软,顺着白光往东山脚跑去。
村庄屡屡得救,于是村民们甚至想筹资起工,建一座石神庙。后来,花石玉被匪徒破坏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在村里作恶。因为小果村中还有一位“保护神”,按辈分我还得称他一声大爷。他长得牛高马大、满脸暗疮、胡子拉碴、面色黧黑,远远看去,俨然一头直立行走的黑熊。大爷天生神力,早年上山打柴,别人每天一个来回都够呛,他却可以每天两三个来回。天色破晓,他就翻身起床,胡乱吃点饭食,就带上绳索刀具上山了。连绵起伏的罗坪山腹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竹。村民们上山大多是为了砍山竹,也有的是为了砍柴。大爷动作麻利、刀快如风,刀子到处,山竹、栎木就被他一茬茬放倒,眨眼工夫,便将两挑山竹或栎柴绑扎好,然后挑上就从山腹中那狭长的山道上晃荡下来,如同扑腾的山风一般轻快,眨眼走出两三里路。别人歇息他不歇息,放下担子又赶山路来接第二挑。如是几番倒腾,却总会赶在别人前面到家。
听说山匪洗劫了村落,正在南沟边地里干活的大爷拿起手中砍刀,一路狂追,终于在花石坡追上了他们,20多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被他全部撂倒在地。匪徒赶紧拾起刀枪一溜烟返回山里,再不敢进犯小果村。但他们却不甘心,10多年后,大爷变老了,匪徒又再次举兵进犯,一进村庄便四处抢劫,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村子里娘哭儿泣,老老少少如鸟兽散。正当匪徒猖狂施暴之时,忽有人报告匪首,称村头一个庭院内,居然有一个老头端坐在火塘边,气定神闲地烤火喝茶。匪首立即带上匪徒来到庭院,远远就能看清那就是当年把他们全部撂倒在地的壮汉。老头两眼里透出一种怡然的神情,像是对他们的嘲弄和轻蔑。是可忍,孰不可忍!匪首气急败坏,快步上前,举起利刃就朝大爷的脑门砍了下来,大爷也不躲闪,伸出一只老手轻轻一扬,一团红雾便在天空中散开。匪首就觉得眼睛里鼻子里嘴巴里顿时一阵热辣,难受极了,连续打了十几个喷嚏,满脸涕泪横流,接着手上又被人砍了一刀,一把利刃瞬间落地。
原来大爷早在火塘边准备了一罐辣椒面和一把锋利的柴刀,当匪首举刀砍来,他利索地把那罐辣椒面往他脸上撒去,又在他手上砍了一刀。匪首睁不开眼睛,鼻里嘴里和眼里的辣呛远比手上挨的一刀难受,全然不顾自己一条命已握在大爷手里。
大爷却对他说:“我不杀你!要杀你,10年前花石坡一战,你已经是我的刀下之鬼。如今四下兵荒马乱,当兵做匪种庄稼,全是苦命人,告诉你的手下,不要杀人,要东西你们拿走便是!”
匪首羞愧难当,正当他转身离开之际,却听得背后一声枪响,一个小头目开枪把大爷打死了。匪首恼怒异常,骂小头目不该在人背后开枪,手起刀落,就把小头目给杀了。此后几十年,山匪依旧在茈碧坝子横行,却对小果村秋毫无犯。新政府成立后,肃清了土匪,远近村落重现安宁。据说,大爷就被村民葬在花石坡中。
义 地
对于一个千百年来沿袭土葬习俗的村落,村子的后山就是坟场。牛滚塘附近,直至花石坡,大大小小的私家坟场大多以家族姓氏命名,譬如“王家坟”“小王家坟”“杨家坟”“五弟兄坟”,还有些以地理地貌命名,如“大坟”“七登坟”等等,村里有老人去世,子孙后代自会把他葬到自家的坟地里。
然而从花石坡到小王家坟之间,有一块坟场居然没有姓氏,被村民们称作义地。据说这曾是一块风水宝地,谁家有人葬到这里,后世就会特别旺,诚所谓“为士者程高万里,为农者粟积千钟,为工者巧著百般,为商者交通四海”。村里曾为这块地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好几次械斗,闹出了人命。最终告到了县衙里,县太爷亲自下来裁决,就把这块地划为义地。
在小果村村民的信念里,那些年少早夭者、客死异乡者、死于非命者,是不能葬到祖坟的,否则就会坏了自家的风水,只能安葬到义地里。后来我们这个村落,曾经接纳了好几个安置户,他们没有坟山,老人去世后没有安葬之地。在家里停柩数日,尸体都要发臭了,也想不出个办法。于是小果村村民共同商定,让他们把老人葬到义地里去。转眼几十年过去,义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几辈人中的十几口人,当然也包括了土山神前那个早夭的少子。于是这块窄窄的土地,居然也成了小果村仁义团结的另一种象征。
 作者:北 雁
作者:北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