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 2021-03-16 09:54 来源:昭通新闻网
”
刘泽,云南鲁甸人。爱好读书、手工,现就读于山西晋中学院。
”
昨天
刘泽
1
闭上眼,世界是昏暗的,睁开眼,世界依旧是昏暗的。我知道,我再一次失眠了。
某个冬天的深处,北方一所寻常的大学里,我蜷缩在窄小的绿皮铁架床上,辗转难眠。天色昏黄如同旧搪瓷杯底的一层茶垢,预兆初雪将至。寒风呼啸,摇撼窗外凋零枯槁的法国梧桐,扯下所剩无几的碎叶。高大苍白的白杨树干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与宿舍里的呼噜、磨牙声交织一起,鸣奏出一段无可名状的夜曲。我紧闭双眼,试图催眠自己,无奈没多久又以失败而告终。
难以入眠时,我通常靠思考来打发时间。任凭思绪像蚊香一样蜿蜒扩散开来,混杂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飘向不知何处的某个角落。常常拖沓到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翌日清晨又匆忙赶去学校,上紧发条般开始一天的生活。邻近中午,囤积的睡意猛虎下山一般扑到跟前,蛮横地赶走仅存的清醒意志,使我常常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伴着老师叨叨絮絮的话语沉沉睡去,直到下课铃声响起。随后便顶着刺眼的阳光和瞌睡带来的空虚感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照常吃饭,午休,上课,吃饭,看书,睡觉。次日在闹铃声中昏昏沉沉地醒来,再次上好发条,迎接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使这样紧凑整齐的日子里,失眠仍会不请自来。它蹑手蹑脚地爬上位于公寓三楼的寝室,溜进虚掩的窗户,一声不响地蹲伏在角落。等到察觉时,它已经像棉花一样塞满了整个房间,无力驱赶的我只好悉听尊便了。
通常这个时候我会浮想联翩,追忆起人生旅途中得到或失却的许多东西。那些回忆裹挟着无比真切的情感,滴滴答答地从床铺间、桌底下、天花板上溢出,并汇集成涓涓河流,直至化为汹涌波涛,推搡着我回到往昔岁月——雨后阳光下的红脑袋蜻蜓,在书店里顺手牵羊被扭获后的惶恐,第一次亲吻女孩时唇间柔软的触感。无声的安静逐渐变得吵闹,几乎震耳欲聋。
回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些画面,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数年之后依然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和对未来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这些画面终究还是像回飞镖一样转回到了自己手上,如同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般投影到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但记忆终归还是一步步远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忆愈发模糊不清——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无从追溯。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往往最难启齿,你不好意识说出口,因为语言会缩小事情的重要性——原本萦绕在脑中一些意味深刻的事情,一经脱口而出,便立时缩水为原本的实际大小。
我这人,对过去总是怀有难以言说的眷恋,如同有一团恍若薄雾的东西萦绕在头脑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状的东西开始以简洁清晰的轮廓呈现出来,诉诸于语言就是:死亡迟早会带走一切。精彩纷呈的阅历也好,一醉方休的洒脱也罢,或是刻骨铭心的悲恸,都将随着火葬场孤零零的烟囱中腾起的青烟消逝在虚空中。所有话语会随之烟消云散,姓氏会消逝无踪,家族会湮没无名,一切关于你的记忆都将磨灭无痕。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死亡,是遗忘——时间是贼,总会偷走一切。但如果以某种方式留下自己存在的证据,就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人生,让自己的精神活在别人的记忆中。就像空白画布上反复临摹后留下的铅笔划痕,无论覆盖上何种颜色,只要仔细观察,仍能分辨出那微不足道的细小痕迹。于是我格外珍视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想方设法以某种方式将其存留。
2
暮夏时节,疫情的持续蔓延让原本板上钉钉的开学变得似乎遥遥无期。我无所事事地宅在家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如同大多数人。新闻联播每天聒噪着疫情发展的状况,要所有人都呆在家里。眼瞅着感染人数逐天上涨,末日的气氛轻微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生活迟早会回归。随着春天的节日气氛消逝无踪,我像只上了年纪的懒猫一样终日窝在床上,除了义务性的看看网课、心不在焉地打扫家务几乎什么也不想干。各种小情绪随着换季逐渐发酵,使得我总有些喜怒无常,家里的气氛不知不觉间紧张起来,两个月不到就和父母争吵了几次。姐干脆消失在饭桌上,总要拖半天才带着阴云密布的面孔降临客厅,让本就生硬的气氛变得尴尬无比,仿佛有个外星人坐在我们身边。如此几番下来,我有些吃不消了,开始盼望一次远行。田野里清凉的空气、叮咚作响的溪水声变得极富诱惑力,继续呆在家里的念头早就不知遁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因此当父母提出要去乡下参加宴席时,我随口便答应了。
目的地是儿时居住过的一个偏远乡镇学校,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直到父母被调离岗位,去了如今居住的县城。路途本有些偏远,但新近开通的高速公路让旅途时间缩短了不少。拥挤的车上不时有人称赞现代化交通的便利,但我沉浸在彼时乡镇生活的回忆中,听什么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我想起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尽头坐落着一所落魄的学校,一逢下雨天就变得泥泞不堪,若是晴天便灰尘弥漫。唯一的教学楼促狭地蜷缩在院落东边,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楼体沾满灰黄难分的尘土,静默无言地迎接过往的行人。刺耳的铃声一响,一群和学校同样蓬头垢面的学生便蜂拥而出,大声吆喝时两手不忘擦拭着呼之欲出的鼻涕,破衣烂衫上栓着半截蜷曲发黑的红领巾。楼前端立着一个小小的升旗台,被晒得褪色的五星红旗颓然吊在旗杆顶,偶尔随着微风抖动一下;南边是两层楼高的教师宿舍,由同样单调的红砖和水泥堆砌起来,但好在前面有一圈不大的花坛装点,多少雅致了些。阳台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床单和洗得褪色的衣服,阵风一吹便跳起不太雅观的舞蹈,我隐约记得曾在这些被单间玩捉迷藏。除此之外便是花坛对面的两层行政楼,全校唯一不那么显得灰头土脸的建筑物——外墙上粉刷了一层白石灰,多少气派了些。
虽然曾一直和父母住在教师宿舍,但我很少探索这些乏味的建筑,真正的乐趣在校外的稻田里——十多亩的水稻顺着山脚下的一条河流整齐地排列在四周,像一条碧绿的丝带朝着西边蜿蜒而去,看不到尽头。白天稻田里一片寂静,能听到清风拂过稻浪的刷刷声和远处耕牛低沉的吟唱;夜晚稻田则成了青蛙的自由演唱会,聒噪的蛙鸣响彻田野,一路伴随着晚归的农民回到家中。彼时的我总期望能在稻田里碰巧抓住一只螃蟹(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稻田里不长螃蟹),总是不厌其烦地佝偻着腰,沿着田埂一遍遍巡视着水里,眼巴巴地盼望着某只倒霉的螃蟹突然出现,好让我大显身手。同住在学校里的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也有同样的想法,不时陪我在田野间闲逛,我们自然而然成了朋友。他给我看他那手掌大小的宠物飞蛾和珍藏的神话怪物面具,得意洋洋地吹嘘说曾用一个狼人面具吓破了路人的胆,让我崇拜不已。可惜结伴巡视稻田的日子没能持续太长:一次他从水里抓起一团水草在手掌间揉搓,揉着揉着觉得不对劲儿,摊开手一看,一条乌黑肥硕的蚂蝗赫然映入眼帘。我俩跳了起来,一边惊叫一边慌忙逃窜,活像那些被面具吓破了胆的学生。惊慌中他冷不丁把蚂蝗甩到了我的背上,让本就六神无主的我彻底挣脱了理智的束缚,像玩具盒里弹出的小丑一样手舞足蹈地逃回了学校。从此之后他便再也不去稻田里了。
汽车的喇叭声打乱了我的思绪——到乡镇了。我摇下车窗,准备防范扑面而来的灰尘,不料什么也没闻到。空气中隐约荡漾着农家炒菜的香气和吱吱呀呀的喇叭声——任何一个乡镇集会上都能感受到的氛围。撑开车门,双脚结结实实地踏在了整洁干燥的水泥路上,而非我预想的泥泞湿滑的土路。我一头雾水,环顾着四周错落有序的平房,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但证据确凿,眼前的乡政府办公楼前的牌匾上刻着鲜明的字样,驳斥了我的猜疑。我绞尽脑汁也记不起这座一本正经方方正正的办公楼,只得假设是新修的建筑。街道上一扫从前的嘈杂混乱,平整的柏油路顺着两旁栽种的杉树蜿蜒而上,紧挨着两边小孩换牙般新旧共存的商铺。餐馆前昔日涂有橙色染料的木制连栅门已被银灰色的不锈钢卷帘门所取代,看上去竟和城乡结合部随处可见的仓库别无二致。地基显然垫高了不少,与我记忆中低矮泥泞、坑坑洼洼的街道相去甚远。
随着人流缓步来到举办宴席的餐馆,路上不时碰到朝我们打招呼的人,我把待客时用的训练有素的微笑在脸上得体地浮现出来,俯身听他们不太流利倒也真挚的问候,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显得陌生,唯独街道弯曲的弧线折射出熟悉的阴影,提醒着我这里仍是我儿时的故居。吃完宴席上平淡无味、早已发凉的饭菜,我忽然回想起那段和父亲住在拥挤的教师宿舍的时光。他会在昏暗的橘黄色灯光下,趁我睡前用有些拿腔捏调的普通话读上一篇伊索寓言。而我只依稀记得故事的内容大概是关于一只狐狸和螃蟹,随后便伴着屋外噼啪作响的雨声沉沉睡去。
我愈发渴望见到那座宿舍楼,宴席一结束便在熟人的带领下兴致盎然地朝学校走去。穿过几条全然陌生的小径,学校顿时跃入眼帘:宽阔整洁的水泥大道连接着闪亮的铝合金电子栅栏门,门栏两旁保留着蓝白两色的拱形门檐,庄重而不失气派地横跨过保安室;几座六七层高度的教学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清一色的蓝白涂装。阳台处涂着司空见惯的红色励志标语,甚是引人注目;龙柏和针叶杉在路旁一字排开,神气活现地昂首挺立着;几个身着校服的学生径自走来,洗的发白的领口颜色褪得恰到好处,鲜亮平整的红领巾服服帖帖地伏在胸前。他们小声地讨论着明天的课程,不时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木木地挪动脚步,半张着嘴,瞠目结舌地仰望着学校,随后深深地吁了口气——长的如果一直延伸,足可到达月球。保守地说,我非常吃惊。
昔日灰头土脸的教学楼、教师宿舍、行政楼早已不见踪影,一个标准的现代化学校从天而降,把那些老掉牙的建筑全都压进了地底下。若不是父母自豪地向我介绍新学校的来历,我绝不至于把记忆中那些简陋的建筑同这应有尽有的标准中学混淆。学校显然扩建了相当于之前两倍的范围,光教学楼就有两座,以及一座食堂,一个标准大小的篮球场,甚至还有个足球场。几个篮板下挤满了跃跃欲试的男孩,欢笑声洒满了球场。锃亮的旗杆笔直树立在操场上,鲜亮的红旗在晚风的吹拂下骄傲地舒展开来,光景甚是了得。漫步在坚实干净的水泥路面上,我感到有些荒谬。此处已找不到旧日校园的分毫痕迹,如同被地图上彻底抹去一般,消逝无踪。最后我在一块介绍学校历史的展示栏上找到了旧学校的照片——火柴盒大小的印刷图片,贴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像一个显赫家族里曾被人刻意遗忘的丑闻。由于风吹日晒早已褪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
3
我走出学校,在暮色苍茫的街头慢慢行走。关于这一带环境的记忆渐渐复苏过来,领着我向稻田走去。由于房屋的翻修以及街道的扩张,田野的风光已然大不如前,但我仍寻得了一丝安慰——至少还存有些许。昏暗的暮色下三个孩子拎着一个铁皮罐子漫步在河边筑起的堤坝上,空旷的田野里既听不到稻浪翻涌的响声,也没有蛙鸣。沿着河道缓缓走去,我回想起那些花整个下午在稻田里搜寻螃蟹的时光,水藻中藏匿的蚂蝗,以及那个收藏有狼人面具的男孩。它们就像画稿上被抹去的素描,仿佛从未存在过,也没人记得。曾在这里度过几年时光的我现在却成了局外人,不属于这里的街道,不属于这里所有的日常生活。前所未有的落寞感汹涌而来,我到这里来究竟是干什么?
前方传来的嬉闹声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循声看去,先前的三个孩子正和另一帮年龄相仿的少年传看着那个铁皮罐,热烈地争论着什么。我不禁上前查看,原来罐子里装满了小龙虾。少年们正炫耀着自己的收获,不时伸手把企图逃走的龙虾赶回去,越狱失败的龙虾四仰八叉地跌倒在罐底,一张一合的螯钳徒劳的挥舞着。河道边又传来一阵骚乱,几个孩子兴奋地大叫有蛇,引得所有人围拢在狭窄的河道边上。好奇心驱使着我跟上去,在一个少年忽闪的手电灯光下看到了那条纤细的水蛇。它正扭着优雅的曲线游弋在破碎的渔网和水草间,慌不择路地爬到一堆漂浮的垃圾下,与岸上的众人对峙起来。少年们激动的大声叫喊,但没人敢上前捉住这条看似穷途末路的小蛇。或许是出于对过往的怀念,亦或是被少年们的气氛所感染,我不知为何隐隐兴奋起来,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一局面。
又有人惊叫起来,居然还有一条蛇。这条蛇显然更大,此刻正沿着水流快速游过来。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情顺着血管涌上身躯,脑袋却异常清醒,像西部片里准备跳出火车的牛仔一样紧张又冷静地绷紧身体。一句电影台词挑准时机似的猛然跳了出来:要么去做,要么一辈子不做。犹豫了两秒后,我麻利地脱掉帆布鞋,撸起裤管,在少年们的惊叫声中不紧不慢地下了水。冰凉的河水刚刚满过脚踝,使得头脑清醒了不少。我轻轻拾起渔网,像母亲给婴儿穿衣服一样小心翼翼地罩住稍大的那条蛇,暂时限制了它的行动,然后捡起河道里的垃圾堵住小蛇的去路,顺势按住蛇头,一举将其擒获。一旁凑热闹的孩子给了我一个空瓶,我便把蛇一股脑塞了进去。大蛇此刻已经脱离了渔网的控制,肆无忌惮地在水道里横冲直撞。我和它周旋了一会儿,最后也如法炮制地将其塞进了瓶子。
上岸后,天色已如墨汁般漆黑一片,远处隐约传来零星的狗吠声。少年们打着手电,兴高采烈地给我带路,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蛇。一个孩子不住打量着我手里的瓶子,我便提出把蛇送给他,但他没有接受。“这是你的东西,我不能要。”我注视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听见他们连笑带骂地交换着话题,不时爆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最终如同消失在道路尽头的灯光里一般远去。先前潮汐般涌上来的热血已然消退,只留给我昏沉的暮色和难以言表的空虚感。
回到家后,我仍不知该拿这两条蛇怎么办。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神气活现的水蛇变得无精打采,不久后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不由懊恼当初干嘛要抓它们,一时热血冲动也好弥补过去的遗憾也罢,现在都已经变得苍白无力、难以追溯了。
最终我把稍大的蛇做了标本,并仔细做了标注,用火漆封瓶保存。一切完工后,我还是感到不知所措,苦闷的心情难以排遣,失眠也愈发严重。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我带着仅存的蛇去了湿地公园,在一片沼泽地里放走了它。记得那日天气甚好,太阳慷慨地把光线洒满鱼鳞般波动起伏的湖面,折射出无数耀眼的金斑。芦苇从在风中絮絮低语,顶端白色的草絮微微摇摆,像一群意欲飞翔的白鸽。我刚一拧开瓶盖,蛇便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一溜烟滑进了水草丛中。小憩片刻后它便高昂着头,划着优雅的弧线游进了沼泽深处。我远远注视着水面漾起的波纹,想起了《舞!舞!舞!》。羊男如是说到:“跳舞!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没有的,要是考虑这个脚步势必停下来。不管你觉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疏软开来,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救药。你的确很疲劳,精疲力竭,惶惶不可终日。谁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但只有跳下去,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我喃喃自语到。
待反应过来时,已是暮色四合。我久久地坐在湖边青黄不接的草地上,注视着斜阳西下渐渐带走眼前的景色,留给我又一个不眠之夜。远处传来儿童嬉笑打闹的笑声,两个孩子挥舞着荧光棒绕着树篱动物来回追逐;湖边不知何时聚集起三五成群的游人,大都是吃过晚餐外出散步的家庭。每个人都显得悠然自得,脸上荡漾着满足的微笑,空气中弥漫着惬意的氛围。我伸了伸麻木的双腿,忍受着血液积压带来的眩晕缓缓站立起来,伫立片刻后迈着轻快的步伐朝家走去。出乎意料的,那晚我没有失眠。
4
我开始找寻那些以前拍摄的照片。大多数是父母给我拍,我却没时间认真欣赏的老照片。从我三四岁穿着脏得辨不出颜色的破棉衣的照片到十八岁时身着白T站在高考考场前的照片,一一整理好,归类入档。看着照片上各个年龄时的自己,莫名其妙的生分感扑面而来,倒像是某个依稀记得面孔的老友。我开始看那些许久未看的老电影,从《低俗小说》到《肖申克的救赎》《情书》,一部接一部的看完,存进电脑的硬盘里。我开始阅读那些本希望有时间能看的书,重温我特别中意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还找到了本《三体》。我抽出衣柜顶端积满灰尘的吉他,仔细擦拭后调试着琴弦,尝试记起关于吉他的一星半点弹法。我在天台堆积杂物的地方翻出一块装修用的木板,锯出合适的样子后细致的打磨了一番,做成了简易画板。随后挑了一幅合适的印刷布画,用图钉固定在画板中央,将其挂在空荡荡的墙上。画面中女孩的背影怀抱着吉他,端坐在杂乱昏暗的房间里。我一直想要一幅手工绘制的肖像油画,但目前也只能用印刷的廉价画来充数。但母亲似乎不太能理解,质问我画上的女孩可是我的女友,我只好白费唇舌地向她解释一番。
日光灼烈的盛夏,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了无生气。我忙碌着重拾旧好,常常在房间里一呆就是一整天,不料皮肤却莫名其妙的晒黑了。虽然不怎么外出,但生活过的大体充实,埋头过去让我忘却了对现在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无力,心情不由地开朗起来。电影看腻,吉他弦也弹断了几根时,便一点一点做手工,陆陆续续地做了些模型,将其放置在书架一侧。那之后,我又花了几周做了两张弓,将其挂在墙上作为装饰。我有陈列物品的习惯,喜欢看着自己创造的东西安静地悬挂在架子上。这样房间也因此多少殷实起来,像是我自己的了。闲暇时我便带上弓箭,在天台上搭起的简易箭靶前练习射箭。虽然技术叫人不敢恭维,鲜有正中靶心,但倒也乐在其中。时间转瞬即逝,枯燥的生活却由此充实起来,夜晚睡得格外踏实。我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目前我跳得还不错。
更早些时候,当我还不懂得冷暖自知、痴迷于街头小贩的地摊时,做这些事情大概不会被视为幼稚之举。如今我重拾起这些早已干枯褪色的爱好时,感受到的只有时间带来的砠䂳,仿佛咀嚼过期许久的面包,只有粗硬的口感和陈腐的酸味。但我还是乐于拾起它们,细致地审视岁月带来的年轮和难以弥补的裂痕,为其立起纪念碑,以防它们永远淹没在时间里。朝花不禁露寒,只待夕拾。
若是碰上晴朗的天气,我便会拾一把木椅到天台上晒日光浴。清晨的阳光尚且和煦,暖洋洋地洒满整个天台,温柔得恰到好处。随着城市的复苏,阳光也渐渐灼烈起来,刺剌剌地让人睁不开眼。我也只能窝进遮雨檐下的荫凉处,听着远处清真寺的阿訇在唤醒塔上做宣礼。诵经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像一个忽远忽近的长音,在城镇上空飘荡。
我扬起脸,在飘渺的唱经声中浮想联翩,过去的画面真切地浮现在眼前:七月流火,数日丰沛的雨水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簇拥在灰白色的楼群四周,远处茂密的松林在柔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钴蓝色的天穹伸懒腰似的尽情舒展开来,目力所及之处尽被塞得满满当当。云朵似乎被烈日煮沸了,翻滚着幻化不定的絮丝,白的耀眼。清风吹过晾衣绳上晒得发皱的被单,把我的头发揉作一团,旋即向楼宇间吹去,发出空洞的呼啸声。我懒洋洋地躺在一张快散架的木椅里,心不在焉地翻弄着刚买的漫画,兴趣索然地看上几页。表哥和姐躲进了遮雨檐下的阴影里,避开斧头般的阳光,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抓获的小龙虾要如何分摊。我随意应答了几句,意识早已飘到了千里之外的不知什么地方。成群的鸽子耐不住寂寞,纷纷排成整齐的三角形,扑啦啦地从头顶划过,回旋镖似的又飞回巢中,探头探脑地张望着我们。我们三人就这样坐在那里,窝在天台上的阴凉处,像个真正的自由人那样漫不经心地打发着夏日午后的时光。不必担心学业的繁重和就业的艰辛,也无需焦虑家庭中莫须有的压力,没有朋友意味不明的眼神,没有中意的女孩随意敷衍的回答。我们从未如此无忧无虑,仿佛造物主般悠然自得。
但这样的时光终究一步步远离了。如今坐在天台上的我,注视着同样司空见惯的风景,却毫无触动、无动于衷。不到片刻就焦躁不安起来,担心错过手机里的消息和午间的饭点,只好匆匆离去,埋头于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生活。照常吃饭,午休,上课,吃饭,看书,在漫长的黑夜里辗转难眠。
记得高中时曾和一个小巧女孩同桌。她头发短的出格,像男孩一样,一双忽闪的眸子让人联想到树林深处警觉的小鹿,与《怪奇物语》里的小11倒是有几分神似。她患有抑郁症,时常在课上毫无征兆地无声啜泣,引来众人不解的目光。尽管成绩名列前茅,但一学期还没过半她便申请转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她告诉我说自己总睡不着,脑子里纷繁混乱的思绪让人难以入眠,濒临崩溃。“那我可真不明白。”我心不在焉地说着。“你都在想些什么?”
她目光澄澈,定定地说:“什么都在想。”
我想,现在我明白了。
 来源:昭通作家
来源:昭通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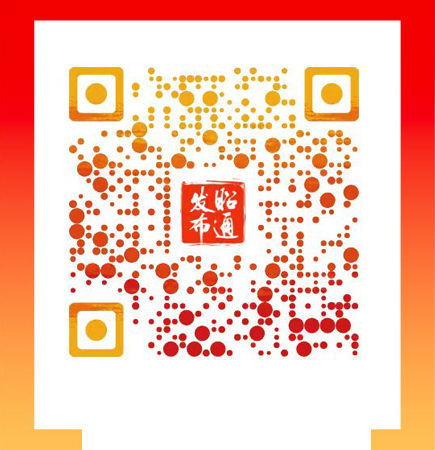

联系电话:0870-2158276
登报作废:0870-3191969
联系邮箱:ztnews@163.com
主办: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承办: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地址:昭通市昭阳区北部新区朱提大道昭通广电中心;Copyright © 2017-2028 昭通市融媒体中心
新闻爆料、涉未成年人举报、涉毒及有害信息举报:0870-3191933 举报邮箱:ztnews@163.com,涉毒举报,疫情求助
登报作废:0870-3191969,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举报电话:0870-2159980
昭通市“打假治敲”举报电话:0870-2132590,举报邮箱:305906736@qq.com,举报地址:昭通市昭阳区公园路45号市委宣传部(市委大院内)
滇ICP备19003243号-3 ;云南省公安厅备案号:53060203202019;互联网信息新闻许可证编号:53120180014;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总)网出证(云)字第002号
本网站法律顾问——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赵文律师,未经昭通新闻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