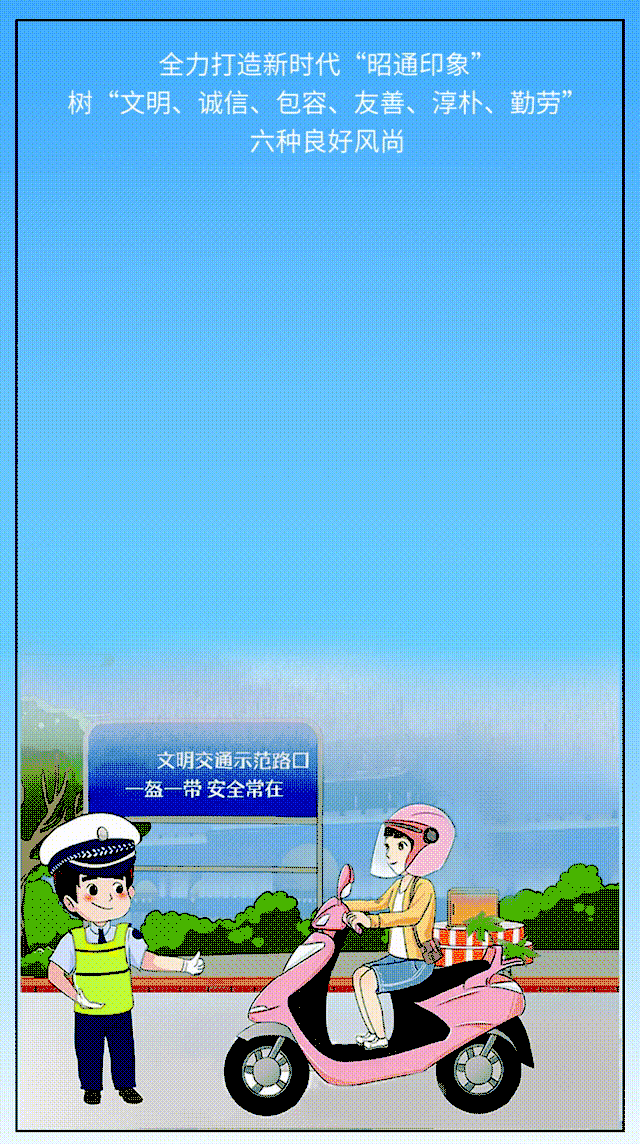2025-12-01 10:15 来源:昭通新闻网


在乌蒙山脉的褶皱深处,金沙江的涛声与千年朱提银的回响交织成一片文学的沃土。这里,群山以沉默的姿态托举着思想的翅膀,土地以裂变的阵痛孕育着叙事的力量——昭通,这座被群山环抱的“文学之乡”,正以“昭通作家群”的集体光芒,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向西南方延展。当电影《白桔》的镜头掠过金沙江畔的白桔林,当银幕上的光影与沈力笔下的文字共振,我不禁追问:是什么让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昭通人,能以笔为犁,在文学的荒原上开垦出如此丰饶的风景?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专访了《白桔》作者沈力,以此解答我对作者创作思路的解剖。

记者:继在昆明举行《白桔》的创作交流会及电影在昭通市放映后,好评如潮。沈力老师是地道昭通人,对这块土地有深深感情,我想问一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
沈力:《白桔》在昆明举行的两场观影会后,大家对这部小成本的电影好评如潮,让人始料不及。作为地道的昭通人,我从小生活在大山包这个极寒极苦之地,从小父亲就对我说,将来考不起大学就不要读书了,回家来做生意。当时家里开了个小卖部,赶集天要将那些笨重的铁锅等货物搬到门前摆地摊,晚上收摊又搬回家,那时候人小,搬也搬不动,这种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从小过怕了。从那时起,心里就有一种危机感,就在想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给自己一个答案,考不上大学就写文章,可以不用干那么多农活。那年中学毕业进城考试,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就偷偷存了一笔钱。考试结束后,在城里的书店买了一大堆中外文学名著带回家去,锁在一只大木箱里。晚上,悄悄拿出来读,读完又锁回去,跟做贼一样,怕家人看见花巨款买一堆书要挨揍。晚上,整条街晚上都是漆黑的,唯有我的窗口半夜还亮着灯,我还在不断看书。我意外地被北方一所高校录取了,在高校那几年,我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不仅如此,我还到地摊买旧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来读,整个宿舍的床上都堆满了书,睡觉要侧着身体睡。离开高校回家时,由于书太多,带不走,就用凉席在学校摆地摊卖书,卖不完的书,最后送给同学。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千年一吻》,就是1999年底在学校完成的。当时,同学们睡着以后,我就打着手电筒写诗,3个晚上写了2000行长诗,准备献给2000年,献给新世纪,这是当时国内最长的一部诗集。在高校几年读的书,彻底改变了我,重塑了我,改写了我的人生路径。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创作《白桔》这个题材?
沈力:2013年,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他乡是故乡》之初,我就已经走遍了永善的山山水水,采访了200多名干部和移民群众,采访过程中,我被永善移民群众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故事所打动,为永善干部乐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所感动,为根植于永善人民身上的这种家国情怀所感动,他们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国家的命运中去,家与国同频共振,不计个人得失,这种牺牲远远超越了个人,从而变成了一次集体的担当。“舍小家、为大家”是永善移民群众的精神底色,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调和底色。这样一种毫迈的情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又怎么能承载得了呢?那些悲天悯人,感天动地的故事又去讲给谁听呢?这样的故事,怎能没有一部小说来叙述,怎能没有一部电影来呈现呢?这就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动力。
脱贫攻坚胜利,乡村振兴开启新征程,经过多年沉淀以后,这些故事在我内心深处不断地在发酵,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中篇小说《白桔》,我希望通过小说,去描绘那段在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可歌可泣的移民搬迁史,让更多的人知道,永善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段伟大的历史。小说是电影的母体,小说为电影改编提供了基本的文本,我希望能够通过镜头,去捕捉那些无法用小说语言来描述的移民群众身上的微光,或者他们一个悄悄流转的眼神,一次对着大山默默地倾诉,一次在无数的绝境里还依然选择向上的挣扎。

记者:在创作过程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沈力:小说和电影剧本不一样,小说人物越少越好,要做减法,电影多一个人物多一个看点。创作中篇小说的时间很快,从提笔到定稿只用了一个星期,一气呵成。初稿出来后,我投给《边疆文学》杂志,责任编辑段爱松老师看了以后,提了修改意见,并建议将小说标题《白桔的乡村》改为《白桔》,很快小说就在《边疆文学》2022年第4期小说头条发表了。可以说,小说创作是很顺利的,难就难在电影剧本改编,《白桔》从小说到剧本修改了半年多,中间反复修改,删了很多精彩的桥段,这些桥段剧情虽然很好,但与所要表现和传达昭通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不相符,后面又推翻重来,直到满意为止。小说不必考虑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但电影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电影是编剧和导演的艺术,剧本改编不能要求导演完全照搬小说原著,要给剧本二度创作留有余地和空间,也要给导演留有发挥和创作的空间和余地。为了满足剧情需要,符合当下乡村振兴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在电影剧本中又增加了村主任等一些重要人设,补充小说中可以不用出现的人物,以此丰富剧情。可以说,剧本远比小说要难改很多,矛盾冲突更加强烈,结构更加紧凑,反转更多。

记者: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过程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些地方?
沈力:乡村振兴题材基本上没有票房号召力,但这样一个如此精彩的故事,总得有人来写,总得有人来记录。电影和小说是两种文本,两种艺术呈现形式,一个是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去获取故事,一个是通过观看画面去获取故事,小说的冲突没电影那么多,反转也没那么多。电影改编本身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有的剧本可能只用到小说的一个标题,一段话,一个核心故事。《白桔》改编过程中,基本保留了小说原著的核心故事,保留了人物主线,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延伸。永善是多民族地区,有大量的苗族和彝族群众,将故事设定为民族题材,合情合理。很多人都很惊奇,乡村振兴主题不好写,弄不好就会写成报告式的材料。在编剧过程中,我就将乡村振兴这个大背景无限缩小,掰开了、揉碎了,将它们一点点融入3个年轻人的青春事业中去,融入3个人的感情纠葛中去,给观众看,这样一来,故事就出来了,也好看了。用3个人的爱情小故事,去讲述乡村振兴这个时代大背景。这个大背景不只是乡村振兴,还有国家西电东送重大战略工程,还有中国最艰难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工程。这是这部电影我最满意的地方,一部小成本电影讲述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背景。

记者:站在这部电影成功的起点上,我想问问沈老师,你以后在创作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沈力:这部电影也许只是起点,也许也是终点,因为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中国电影市场的格局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场已经不在长片里,而转向了更短的短剧市场,我们在央一、央八频道经常看到的那些大制作的国内顶流编剧也被迫转向了短剧创作。因此,今后我的创作主要还是放在小说创作上,当然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对电影的追求和剧本的创作。
采访结束时,暮色中的昭通古城正被万家灯火点亮。沈力望向窗外鳞次栉比的楼群,却仿佛看见乌蒙山巅的星子坠入人间——那些在田间地头生长的故事,那些被岁月打磨成琥珀的记忆,终将在文字的永恒中找到归宿。昭通作家群的根系,早已深扎于朱提文化的岩层,汲取着马帮铃铛的余韵、红色扎西的炽热与乡村振兴的脉动。当新一代写作者以科技为舟楫、以跨界为桥梁,这片土地的文学火种,必将在群山的回响中,照亮更辽阔的天地。
记者:陈允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