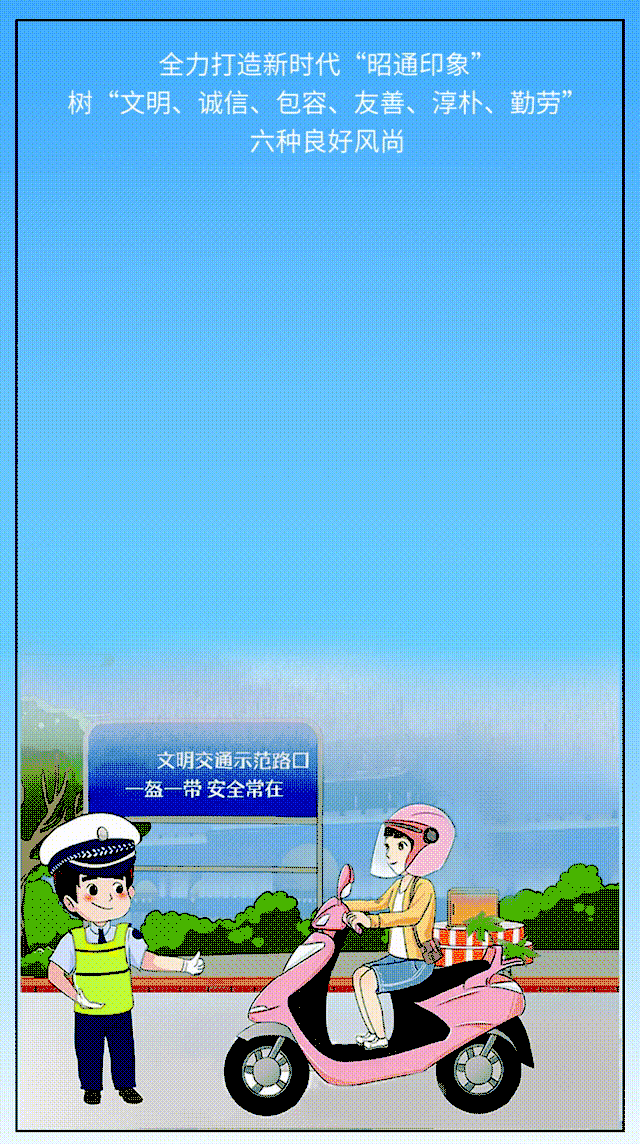2025-11-15 10:07 来源:昭通新闻网



生活在群山褶皱处的一个山坳里,青山就是全部,一条河向北淌去,只有云知道怎么来到这个地方。
山坳里的世界,好多事情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吃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就连对事物的称谓也不一样。比如蜻蜓,我们叫它“马儿灯”。蜻蜓和马、灯有什么故事吗?我不晓得。从我记事起,这个小东西就叫马儿灯,它只在夏天出现,然后继续蛰伏。
我们这儿是一个小盆地,热天总是格外多些。一到夏天的午后,马儿灯就飞得很低。我们常撕一种叫“晴天草”的东西,若是不能把草从头到尾完整地撕成两半,大伙儿就说天要下雨了。但我早就发现,这法子比不上看马儿灯来得准。
我喜欢盯着这小小的精灵瞧,只要它们贴着地面飞,肯定就要下雨。几声闷雷,一阵风吹过,大雨便哗啦啦地下。不过这雨下不了多久,人们又重新聚拢起来,继续摆龙门阵。马儿灯飞得很低的时候,只需拿起扫帚在空中扫几下,就能逮着好几只。
只是用这个法子抓的马儿灯,它的翅膀容易被打坏,即使放了,也飞不高,而且从此不受同伴待见,只能自个儿窝着活。墙角的柴火堆里,就藏着好多这样的马儿灯。翅膀坏了的马儿灯,偏在下雨前飞得最欢——只有在没有同类发现它残缺的时候,它才想让人看见自己还活着。
抓马儿灯的法子,是麻老大教我们的。
这人,村里人说他是个痴子。他脑袋不太灵光,心性像个孩子。他的几个弟弟里,老二去世了,老三外出打工,只有做木匠的老四还和他一起生活。我头一回对他有印象,是有一次我们跑去他家玩,刚好赶上他家吃饭,他正在锅里挖饭底下的锅巴。我也爱吃锅巴,脆得很。可那时我觉得自己不会和他做朋友,他爱吃锅巴,就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分我锅巴吃。
麻老大总是独来独往,甚至很少有人问他一句“你吃饭了吗”,因为他说话只会吱哩哇啦地叫。他时常犯痴,还会动手打人,大人们总叫我们离他远点。可我却在心里觉得,就算他不会分锅巴给我吃,这世上总算不止我一个人被说“吃得怪”了。
我们在田里掏黄鳝时,有时会遇见麻老大。我们半天掏不出来一条,他就走过来哼哼两声,然后告诉我们:先把手轻轻伸进泥里,田里的泥软和,要用指纹去感受泥土的动静,慢慢往下掏,等到一种冰凉滑溜的触感传来,立刻抓住,迅速掏出来。
黄鳝身子很滑,稍一迟疑它就溜走了。临走前,麻老大总会朝我们走来,看见我们抓得少,就默默地把自己掏出来的黄鳝,倒一些在我们的袋子里。
我不吃黄鳝,更怕蛇,而黄鳝偏偏长得最像蛇。所以我抓到的黄鳝常常养在一个小伙伴家里,用一个大红盆装着。这盆比一般的盆大,家家都有,冬天烧一壶热水倒进去,一家人都能围坐在一起泡脚。日子过得再好的人家,那红盆上也有用各色塑料补过的疤。那些补丁颜色杂乱,放到现在的话,算得上是一件抽象艺术品。
而这片山里,唯一称得上艺术家的,大概只有那个补盆的中年男人了。他每次出现,都会背着一个背篼,边走边吆喝:“补胶盆!补胶盆!”一路穿过沿途的人户,直到有人喊:“师傅,等一下!”他才应声停下。放下背篼,等顾客拿出家里的破盆,他便从背篼里摸出一根喷火管。往右拧一圈,气体嘶嘶溢出,用打火机一点,“砰”的一声,一股火苗瞬间蹿出来。他随手取一块旧塑料,贴在盆的破裂处,用火慢慢烤软、压实。待补丁将硬未硬时,再用大拇指顺着边缘反复按压,留下清晰的指纹。我敢说,他的指纹,散落在三桃乡的家家户户。那些被修补过的盆盆罐罐,也因此不敢轻易再开裂——生怕又被烙上一块丑陋的补丁。
补盆匠待人却不是这般“凶狠”。麻老大一听见“补胶盆”的吆喝声,就高兴得不得了,赶忙跑到河对面的公路旁,守在写有“斑竹村”的牌子下等。补盆匠来了,对他说一句“你吃饭没有”,麻老大立刻呜噜呜噜地比画,意思是自己“吃过了”。补盆匠顺着河岸吆喝,麻老大就默默跟在后面,一直走到河水铺展开的那片开阔地,才停下脚步。
我们这儿,是千万年流水温柔冲刷出来的方寸之地,河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
我们这地方,原本叫斑竹塘——河边曾长满斑竹,河里有许多深浅不一的水塘。我们是在那些水塘里玩水长大的。一群孩子,还没到岸边,就已一丝不挂。夏天阳光炙热,河水却温润。背上的皮被晒掉了好几回,新露出的皮肉被阳光晒得发烫,又被河水浸得冰凉,那一冷一热的激灵,直往胸膛里钻。
小学老师没事就来河边巡查,抓到泡在水里的学生,立马叫上岸。家里的大人知道后,用竹条抽得孩子身上起一道道红印,可孩子们还是往水塘里跑。麻老大也在,他是唯一一个要穿汗裤下水的人。他不跟我们说话,只是泡着,偶尔钻进水里游几下又浮出来,静静看着我们嬉闹。
玩够了水,我们就去山沟里抓螃蟹。在我们这儿,螃蟹被叫作“爬海”——是因为它真的从遥远的海里一路爬啊爬,才来到这山沟里?还是说,它心里怀揣着爬向大海的远大理想呢?
螃蟹住在山沟两侧的洞里,搬开石头就能找到。山沟里流下来的水冰凉刺骨,头顶的太阳却晒得人直冒汗。
我一直怀疑,蝗虫是一种有“受虐倾向”的昆虫。鸡最喜欢吃它了,可它偏不怕,还要发出声音,像是故意引鸡来啄,所以我们叫它“叫鸡子”。有时候鸡没来,倒招来一群孩子。我们抓几只叫鸡子,用狗尾巴草串起来,伸进螃蟹洞里。螃蟹以为送上门的肉来了,死死钳住叫鸡子舍不得放,我们就顺势一拉,把螃蟹拽出来。我们管这叫“逗爬海”。等我们抓够了爬海,天色已近黄昏。下山的路上,常能看见悠闲的麻老大——他喝完酒,一个人静静地在水塘里泡着。
麻老大泡完水,往石板上一坐,石板烫得他赶忙挪了挪屁股。他随手扯来几根狗尾巴草,指尖翻飞间,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就编好了。编笼子时,麻老大只有手在动,像一块静立的枯木,连马儿灯都敢在他头发上驻足。笼子刚编好,他便随手递给旁边的小孩。那孩子如获至宝,到处找蛐蛐儿,非要抓只最大的,才觉得配得上这漂亮的笼子。
人们都说麻老大活得像个孩子——说话的模样像,做事的天真劲儿也像。可干起活来,他一点儿都不像孩子。在我们这儿,所有跟劳动有关的事情都叫“活路”,人要是不劳动,就相当于日子没了“活路”。
盆地里的庄稼熟得早,还没到秋天,地里的苞谷就该收了。麻老四守在地里,把苞谷棒子从苞谷秆上掰下来,随手扔进脚边的背篼。一个背篼快满了,就换另一个空的接着装。麻老大则一趟又一趟地往返着,把摞得冒尖的背篼往家背。苞谷棒子早就高过背篼沿,他还要再往上摞几层,用绳子勒得结结实实。麻老大穿着一件印着“XXX 化工厂”字样的蓝色衬衫,衬衫被汗水浸成了深蓝色,紧紧贴在背上。我们在阿刚家看电视,每次他路过,我都能清楚地看到汗水顺着他的额头、鬓角往下淌,没有一丝拖沓,径直滴落在地上——先是洇出一小团湿痕,转眼就被烈日烤得无影无踪。若是太阳再柔和些,他走过的路,大概会留下一圈圆圆的汗渍轨迹。
等两兄弟把最后一背篼苞谷背回家,倒在院坝里,脱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今天就算收工了。麻老四喝白酒,桥头小店卖5元一斤的散装酒;麻老大喝冰啤酒,两元一瓶。麻老四用高压锅把饭焖上,就光着膀子去买酒,留麻老大在家洗菜。麻老大端个铁盆,坐在门口的水龙头旁慢悠悠地择菜、清洗。麻老四买好酒,又在街上听了会儿龙门阵,才提着酒回家炒菜。随便炒两个加了辣椒的家常菜,舀上两大碗饭,两人便坐在门口的小桌子旁吃着简单的晚餐。他们没有碰杯,只顾着各自喝酒吃饭。每次都是老四先吃完,拿着块肥皂就去河里洗澡了,丢下麻老大在家里洗碗。
山里的黄昏走得很慢,太阳落了山,马儿灯都还要再飞一会儿才消失。这时候的河水早已没了白日的暖意,冰凉刺骨,只有大人们还聚在原先孩子们戏水的水塘里,泡着水闲聊,说今天打了多少背篼苞谷。
麻老大收拾完家里,才往水塘边走去。他把今天穿的衣服搭在一侧肩上,另一侧肩头露着,一道被背篼系勒出的红印清晰可见。等他快到水塘时,麻老四他们已经在穿衣服了。隔着老远,人们看到麻老大的身影,就知道差不多该穿好裤子起身回家了。
麻老四把自己的肥皂递给他,便和其他人一起回家。麻老大什么也不说,径直站在水里,用肥皂在自己身上抹了个遍,又把搭在肩上的衣服当作帕子,使劲搓洗起来。身上的汗渍、衣服上的污垢,就这么一并洗干净了。等他洗完回家时,夜色已近在咫尺,只剩下天边一寸微光,几只马儿灯一直跟在他身后飞,直至黑暗慢慢吞噬他的身影。
打完苞谷,又要收割稻谷。从田地到晒场,麻老大一直重复着繁重的农活,汗水仿佛永远也流不完。我时常想,他背着那山一样沉的苞谷时,会觉得累吗?会感到孤单吗?或许从他第一次把沉甸甸的背篼背上肩头起,日子就注定是这般模样。他只要看到我们这群孩子,就想教我们他小时候玩的东西。我们常常围着他问,那些翅膀坏了的马儿灯,会不会重新长出翅膀呢?
黄昏为群山镀上金边,山色变得温和慈祥。蝉鸣再次聚拢而来,汹涌又杂乱。面对即将降临的黑暗,马儿灯悄悄地躲着,哪怕要下一场大雨,它也不再兴奋地振翅飞舞。
那个补盆的男人,听说很多年前就外出打工了。我总在想,他要是以后回来,还想接着做补盆的营生,认不得我们这儿了可怎么办?算了,就像那些马儿灯一样,人不管走到哪儿,总能找到自己的活路。
作者:曹开俊 昭通学院文学创作班学生